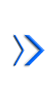排线的织布工
1884

1884年暮春创作的作品中,织布工倒是在织机的外面,正弯着腰整理纱线或清刷织出的布面,可织布工的形象也是死板的,只不过是机器的附加部分。就像摆着常规姿势的人体模特,这些织布工既未表现出个性也让人看不出任何神情。在梵高的这些作品里,令人感到非常亲切的是织机,而不是织布工,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干活儿的工具,而不是织布这项工作。
与梵高所收藏的吕克布施那张刊印出来的作品相比,这种特点给人的印象更清楚。在吕克布施的画里,细巧的织机里是聚精会神干活的人,我感到工匠离我们更近、更亲切。光线往往从一个窗透进屋里,使工匠置身于一种安全的氛围。然而梵高笔下的人则令人感到难以接近,画里也没有这样的气氛。吕克布施是用传统的画法表现靠古老的工具干活谋生的工匠,而在梵高的作品中,织布工变成了工具,织机才是手工艺的化身。
我们也许可以把这种不寻常的处理归因于梵高并不擅长描绘人物,描绘人物明显暴露了他在这方面缺乏训练——这无疑是他的一个致命的不足。但是梵高画人物时的笨拙也有明显的好处,因为对人物的不合传统的粗线条处理出了物体的突出位置和重要性。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梵高对纽南织布匠的粗糙处理使这些人既带传统的特征,又符合当时其行业的处境。画面上引人注意的是物不是人,这样就产生了人和物错位的效果,从而更加激起看画人的同情。用绘画的形式来表现一种手艺,把人物放在次要位置,而把工具突出,也许不失为一种可取的方法。而且人和机器主次位置的颠倒有效地对传统手工业怀念的角度。
梵高的书信印证了这种理解。
他对机器的异乎的强调、对人物的笨拙的不会不被人注意到,因此他的信多少带有点辩解的性质。提奥不愿意展出这些作品,他建议梵高要刻苦而有耐心,这使他的哥哥感到有些委屈。但是安东·凡·拉帕德对工匠和手工艺题材的作品也感兴趣,于是在三月份,梵高决定把自己的素描拿给这位朋友看。拉帕德似乎喜欢梵高这些作品,不过他对不合传统的主次安排及人物处理提出了疑问。梵高为自己的绘画策略和意图做了辩解。他在给拉帕德的回信中坦率地承认:“你的信评价了我那几幅画,这使我很高兴。我只是在画中填上了人物。”接着他又写道: “但是我真正想表现的只是:“落满尘垢的橡木织机是个黑糊糊的怪东西,这怪东西身上装了许多棍棒,它与发灰的背景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怪东西中间,坐着一只黑猴子,也许坐着个妖精和鬼魂,那个鬼魂从凌晨到半夜都在咔哒咔哒地拨弄那些棍棒。”
我在那个位置上放进一个幽灵似的织布工,是因为我曾见到过他坐在那里,我草草地几笔就把他涂抹了出来。因此我根本没认真考虑过手臂、大腿成不成比例。”
在这封信里,梵高并没有对“草草地几笔就涂抹出来”的幽灵似的或比例失调的人物表示歉意。正相反,这是有意为之的策略,因为按照梵高的说法,有话要说的主要角色是织机而不是织布工。他接着写道:
“我十分谨慎地画完机器之后,觉得听不见它咔哒咔哒的响声实在遗憾,于是我把那个鬼魂放到机器里面。好吧,即使说我的画只不过是一张机械图,那也没什么。可是你把它放在织机的技术图纸旁边比一比,你肯定能看出,还是我画更灵异。事实上它绝不是机械图,或者说它比机械图多了“某种东西”[原为法文je ne sais quoi]。”
这样看来,梵高在信中承认他特别关切的是织机,“把那个鬼魂放到机器里面”是颇有点勉强的决定。可是他显然相信自己对织机的表现效果是卓越的。他再一次说明:
“假如你把我画放设计过织机的机械工所画的织机图旁边,我的画肯定有更强的表现力,尽管那画上所表现的只不过是被汗手摸脏了的橡木制成的东西;看着这幅画(即便我在画上没填上那个织布工,或者即便我填上的这个人身体各部位不成比例),有时你也公不由得想到那位织布工,而当作看机械工所画的织机模型时,就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个满身是棍棒的奇妙玩意儿会不时发出一种叹息或哀号。”
他还对凡·拉帕德说:
“我很欣赏你所画的那些以机器为题材的作品。为什么?——因为当你只画了飞轮时,我就会不禁想到使它旋转的那个男孩,总之我会莫名其妙地感到他的存在。而那些把你的与机器有关的作品权看作机械图的人,则根本理解不了你艺术。”
梵高很清楚地着重指出了机械图和富有表现力的画之间的区别,但是他在信一再强调的语气则使人注意到存在于艺术论争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越来越令人产生疑问的人与机器之间关系。机械绘图中的织布机也许可以宣传技术上的改进,然而它们跟劳动力问题、跟工人或者说工匠沾不上边。梵高坚持认为他自己所画的与机器有关的作品恰恰与工人或工匠密不可分。他笔下的织机在表现手法上有象征性、在结构上有怀旧韵味、在不寻常的细部描绘上令人感到真实生动,因此它们体现了手工业生产的传统,并且按照梵高的说法,还使人联想到操作它们的工匠。虽然梵高认定他们两人在创作上有相似之处,不过也许人们仍然理解拉帕德对梵高作品有不满和批评。然而用这种标新立异的方式来表现工人及其历史,梵高的作品就触及了工业生产最有威胁性的一个方面——被盲目崇拜的商品化,正是这种商品化掩盖了人劳动和技术。在梵高眼里,那个春天的织布工不再是迷迷糊糊、梦游患者似的物,也不是变得更高尚或更野蛮的,而是成了像鬼魂一样东西,他们自己还有他们的劳动都被装进了积满污垢的古老机器。
从这一点来看,梵高的信和画暗示着一种相当复杂、多层次的崇敬。重读一下他的信件,人们确实会感到疑惑:究竟是谁在叹息——是人还是机器?按照梵高的说法,织机里有鬼魂出没。织机常唤起人们的回忆,织机是”灵怪“之物,是”黑糊糊的妖精或鬼魂“似的织布工操作。格里塞尔达·波洛克曾提请人们注意梵高的这种说法的阶级特色,他认为这样的措词表明了画家在社会地位、甚至在人性意识上与那些工匠和农民都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这种奇异的比喻跟某种同样具有阶级特色的文学语言如出一辙。梵高在信里只不过是引用了维多利亚时期某本书中的说法。就像他的绘画作品那样,它们还使人联想到工业生产令人困惑的影响:在看画人的感觉里,织布工似乎时隐时现,或者说那织布匠随时都是消失。
梵高在挥毫创作了几个月之后,用这样的话为自己付出的努力进行了辩解,这也暗示着他在挣扎着离开他那些乡间的绘画对象,而将注意力转向自己作品的观众。他穿着斜纹粗棉布的农服,那样子就像一条”粗野的狗“。这身打扮为的是跟纽南的农民们打成一片,可是织布工们却把他看成”schilder-menneke“(小画匠),这位小画匠曾付钱给村里的小伙子,让他们为自己收集鸟窝。梵高当初曾急巴巴地穿起乡村的衣服,取得乡下人的身份,而此刻他的措词则表明他在急切地向中产阶级的市场呼吁,也表明他现在的角色变成了”beeldenmakerlaar“,或者说画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