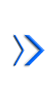献给高更的自画像
1888

在普罗旺斯梵高所画的自画像数量明显地减少了,而在阿尔和圣-雷米创作的10幅自画像里,直接反映画家身份的更是绝无仅有。虽然梵高创作阿尔人物系列作品地点在黄房子,可是又给这些作品的背景加进了异国情调,因为他把自己画成了日本和尚。画家欧仁·博什也出现在这个系列里,可是他被画成了中产阶级的纨绔子弟:身穿黄色上衣,身后是缀满繁星的蓝色午夜的天空,梵高用他来象征"诗人"。(L531)
梵高在普罗旺斯的自画像往往被说成带有精神受疾病侵袭的迹象,这部分也是因为梵高在有关的书信中谈到过发狂的话题,同时部分地还因为其中最出色的几幅刚好创作于他自残和精神上出毛病的前后。然而,即使我们难以反驳这几幅自画像与他的伤病事件有关多说,人们同样难以从中找到技巧或自我表现方面的不正常之处。画面上肯定没有明显的败笔,那几幅在最"非常"时刻创作的自画像恰恰是颇具艺术成就的杰作。其内蕴也颇为深刻。这些自画像中不但没有病态的迹象表露,而且成功地将"发狂"体现为现代画家的一种特征——从更大的社会角度来看,现代画家的个性与处境决定了他们身上会出现若干职业性的问题。
这些自画像里最重要的一幅即是本幅。富有气质的面孔再一次体现了观相术式的描绘手法:稍微倾斜的眼睛(据说这是日本和尚式的眼睛)射出犀利的目光,高高的额头和头皮绷紧的脑壳似乎充满了活力,这种绷紧的活力被红绿两种反常的配色表现得异常显著——石绿色的背景衬托出人物的轮廓,同时与桔红色的眉毛、与脑壳、与胡须形成了强烈的对照,赭色高光使泛绿的深棕色上衣变得格外醒目。人物的身体微侧,为的是突出棱角分明的头,同时又把人物的特征一览无余地表现出来。
梵高知道这幅自画像横眉冷目的样子让人感到很不舒服,而且他曾详细地向提奥和威尔解释过这副样子的由来。这部分地与日本僧人的异域特征有关,但是他还借鉴了另一类有象征意义的角色,暗示是埃米尔·沃特所画的许戈·凡德胡斯的肖像,德胡斯是一个"疯画家"和"温和的牧师"相结合的角色。他告诉提奥自己既不是"疯画家"也不是"温和的牧师",而是摇摆于"两者之间"的人(L514,W4)。对梵高这样一位经历坎坷、命运多舛的画家来说,即使那些自画像创作于那些不幸事件之前,我们也不能把精神狂乱的问题抛开不提。诚然,无论梵高精神上多么狂乱,只要把狂乱的艺术心态与疯画家兼牧师的双重性情搀和在一起,这种现象就已经超出了个人心理平衡问题的范围。
梵高用一个宗教人物形象——实际上是日本僧人和温和牧师两个宗教人物形象——来抵消"疯"画家的形象,通过采用一个宗教人物的身份,梵高便把他的日本式幻想与宗教肖像画法联系了起来,而这种宗教肖像画法备受他在蓬特-阿旺的朋友的推崇。在梵高心目中,日本僧人是俭朴勤恳的人,肯为崇高的事业献身,像耶稣一样,富有灵感,是能够创造理想化事物的典范。
梵高明确表示这幅自画像有多重含义,它所表现的既是他——现代画家,也是超世俗精神的追求者。他向提奥解释道:"我在给高更的信中对他讲,如果在一幅自画像中我可以着重表现自己个性的话,我已经进行过这种尝试,因为在一幅自画像里,不但表现了我自大,而且表现了一般意义上的印象派画家,把它构思为一位僧人的肖像,一位对不朽的如来佛虔诚的崇拜者。"(L545)梵高把这番话写给高更,在证明他们在文化观点上的一致。
自画像往往用作纪念品与朋友进行交换,这一点就使得画家觉得很有必要在自画像上表现出含义丰富的多重身份。梵高、高更、贝尔纳、夏尔·拉瓦尔互赠自画像等于现代画家圈子内用绘画作品进行交谈,尽管这些互赠的自画像没有一张是表现画家正在作画的。拉瓦尔的自画像将人物放在秋天景色的背景上,画面上的画家凝眸注视着看画者。高更和贝尔纳的自画像中都有对方的肖像,然而在这两幅作品中,高更的校长威严是很明显。在高更的自画像里,头的立体感很强,像是要从花饰的背景上探出来似的,而贝尔纳那幅却色调柔和平淡。如果说梵高把自己画成了乌托邦意义上的僧人,那么高更则把自己称作"土匪",并借助雨果描述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给自己和贝尔纳贴上了"悲惨者"的标签。
虽然他们在自我描述上有这样差异——高更的自我描述具有激进的战斗意识,而梵高的自我描述具有更加温和的使命感,但是他们的自画像都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表现了自己的忧虑。他们采用种种不同的角色,创作出一些很有趣的作品,表达了一种自我抬高的乌托邦式理想,同时也暗示了困窘密切相关:由于画家的增多、绘画市场的啬,画家变得越来越穷。梵高在总结他和调理的自画像作品,揭开了它们象征意义的伪装之后,便意识到了这一点。
梵高在1888年画了这张像个和尚的自画像。他向往东方思想中天人合一的境界,为了使自己更像东方人,他把眼尾稍微画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