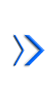软埸塌的钟——达利《永恒的记忆》


萨尔瓦多·达利(1904-1989),西班牙超现实釤义画家和版画家,以探索潜意识的意象著称。达利的画常搜集梦幻中的表现题材,有些画题直接点明为“梦”。但他的“梦”与其他超现实主义画家画上所展现的“梦”的区别在于,达利创造了一种真实感,还寄寓某些他所特别偏爱的内涵。在他所描绘的梦境中,以一种稀奇古怪、不合情理的方式,将普通物象扭曲或者变形。达利对这些物象的描绘精细入微,几乎达到毫发不差的逼真裎度,通常将它们放在十分荒凉但阳光明媚的风景里。在这些谜语般的意象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永恒的记忆》。
油画《永恒的记忆》创作于1931年,尺寸为24X33厘米,该画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达利早期的超现实主义画风。画面展现的是一片空旷的海滩,海滩上面有个莫名其妙的怪物,它似乎有些像人的头部,敏感的人甚至觉得从中可发现达利的影子;而更令人惊奇的是出现在这幅画中的好几只钟表都变成了柔软的有延展性的东西,它们显得软塌塌的,,或挂在树枝上,或搭在平台上,或披在怪物的背上。最后,那块扣放的、爬满蚂蚁的、见不到时间的硬表,被解释为害怕了解真相。
达利创作《永恒的记忆》时采用了“偏执狂临界状态”的方法,即在自己的身上诱发幻觉境界,从潜意识心灵中产生意象。达利承认自己在《永恒的记忆》这幅画中表现了一种“由弗洛伊德所揭示的个人梦境与幻觉”,是自己己不加选择的,并且尽可能精确地记下自己的潜意识以及的梦中每一个意念的结果。而且达利为了寻找这种超现实的幻觉,还曾去精神病院了解患病人的意识,认为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往往是一种潜意识世界的最真诚的反映。达利运用他那熟练的技巧精心刻画那些离奇的形象和细节,创造了一种引起幻觉的真实惑,令观者看到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根本看不到的离奇而有趣的景象,体验到精神病人式的对现实世界秩序的解脱。从此以后达利的画风开始异常迅速地成熟起来,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超现实主义画家。
画中钟表们开始融化。躺在沙滩上的时候,它们一定是太阳晒得太多了,金属承受不了那种热度。一般来说,像液体一样流动的,是时间。“时光流逝”,我们总这么说,虽然有点过时,但至少一目了然。这幅画也是一目了然,而且光滑平整,就像发条一样。可是又不再是这样了,我们需要改变自己的基准点。要是不能再看表了,我们该怎么办?想想所有那些错过的约会。要调整这些表,不可能。不过,也许时间也在溶化。或者它一直都是这样。
问题在于:时间不能治愈一切,尽管人们常这样讲。时间会杀死事物,然后让它们腐烂。时间顺其自然,自得其乐。它不受控制,我们也就是能控制控制这些钟表。时间吸引蚂蚁,放出苍蝇。不过我们不用提防它们:苍蝇的眼睛是奇妙的器官,多面的结构令人赞叹,而且如此精细。画家羡慕它们,一只苍蝇一眼就能看清的东西,他需要借助珠宝工人用的放大镜才行。落在最大的表上的苍蝇,它超过分针,让人以为时间对它来说过得还不够快。但实际上它能自由支配的时间没多少:从它自己无比短暂的生命来看,它一分钟都不能浪费。更不用说五分钟。
倘若时间之手回击,苍蝇很快就什么都做不了了,那三个时钟展示不同的时间。其中一个的内部机制出了问题,这也不奇怪,因为它上面落着一只苍蝇。没事,我们该去别的地方了。考虑到时区的差异,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某个地方能对得上这些荒唐的时针分针。我们一定要知道现在几点了吗?谁说的?就在沉迷于自己的想法和梦境的那一刻,我们就独立了。信仰有时可以移山,但是欲望能超越所有时区,把我们带到想去的任何地方,不管白天黑夜。没人能在那里找到我们。我们梦中的道路上没有路标,很容易就能悄悄溜走,不留痕迹。或者我们可以留下错误的踪迹。人们都摸不着头脑。
但为什么人想要移山呢?这里的山坐落得体,而且肯定无法移动。自从达利记事起,利加特港的山就在那里,真是幸运,因为其他一切都有个古怪的习惯:溜之大吉。
如果这个过程再继续,世界就会变得黏黏糊糊,最后成为名副其实的水母——就像那只躺在表下面的东西,像一条微缩的被子。它很适合做这事,如同当人睡觉时总要滑落到地上的厚重的毯子。到了早上,你感到寒气刺骨。那不是水母吧?呃,好吧。也许它是我们的某个想法。甚至那都不是,而是某个想法的缺席。这令人感到不舒服的小东西,但它看上去没多危险,它的眼睛有长长的睫毛,合在一起。像是一个尖尖的侧面像,有蚌一样的肉。舍不得冒巨大的风险,人们就决不可能知道应该信仰什么,或是相信什么样的外表。生活常常表里不一。既便如此,它也是某种奇怪的自画像。艺术家没有美化自己。他展出自己的噩梦,用他难以平息的画笔给它们定下外形。是他将噩梦击昏,用古典神话中美杜莎的凝视把它们变成石头。他麻痹了它们,再将它们精心摆放在画布上,仿佛精神错乱的清洁样本,这画布谁也不等。画家,像是大脑的昆虫学家。
会有人质疑达利的画的真实性吗?也许只有从未做过梦、从未感到恐惧的人才会,或者是不肯承认这一点的人:当恐惧让我们的床单浸透汗水,他们还是不肯承认,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已经超越了清醒生活的模糊界线。床单必须洗干净,在阳光下晒干。也许那一只钟表也会变干。它挂在橄榄树枝上。树枝很不牢固,枯萎了,很快就要折断。这钟正在溶解,像油一样厚。橄榄油。一切都在混乱。
面对疯狂,艺术家手上有一种武器:他的画家专业。这不是因为身边的现实即将土崩瓦解,所以图画也要这么做。达利不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恐惧,但是他可以很容易地掌握绘画的艺术。学院派的专门技能对他来说不是秘密。也许他会动摇对理智的坚持,但画笔不会从他手中滑落。画家笔下难以看到的笔触是他最后的避难所。他揭示自己不安心神的方式,就是躲藏在油彩层次之间,如此精妙,以至于物质已经超越了模糊的想法。结果,在密谋扩张的现实和将要容纳它的颜料之间,发生了一场战役。确定无疑的姿势,撑住了即将崩溃的外形。画作将梦公之于众,让其慢慢发展自己的秘密。但是它为幻象设下界线,它的四个边将幻象困于其中。
画作不让威胁迫近,达利以悖论为基础,增强了画作的效果。元素越是不一致,设计的细节就让它们靠得越近。描绘越是客观,外形就越是令人不安。这是恶性循环。手的冷静证明它的恐惧,就像无聊麻木的现实一样。完成这幅画,需要走钢丝的人一样的平衡力。
这些物体不再听我们的话。我们不知道从哪边才能接近最简单的现实。总会有某个时刻,我们不想再看到定义被不断打破。为了找到某个易于辨识的地标,我们需要回溯自己的步伐,回到最初。这就是为什么达利的画仍然是传统作品,即使作品中的内容几乎要迸发出来,还要鼓励内心的言说以无法分辨的语言讲出。在这方面,他接近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他的忠诚是双倍的,既在美学层面,又对他个人如是。他画画的方式让人想起过去的大师,这也是因为他在年轻时期就是这么学习的。早年间的确定性保护了他。一幅到下一幅,他的技术从未变化,为他提供防御,噩梦在之面前无能为力。
背景中,利加特港的峭壁证明:儿时的风景不会改变。它们在心中常存,存于我们所有记忆的地平线上。时间让生命脱形,看起来好像被洗的次数太多了。生命被它弄得支离破碎,但又能如何?海滩会闪耀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