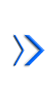小夜曲

小夜曲 1942年,布面油画,195x265厘米,蓬皮杜中心,巴黎 毕加索作品赏析
此画又名《晨歌》,画中两个女人。似乎被解剖的那个,躺在那里,能看得很清楚,至少从可辨别的特征上是这样。但是另一个人物就没有那么明显了。既便如此,也能推断出她是个女人,因为她穿着裙子——这不那么直接的证据。
她拿着一个曼陀铃,放在膝上,看着自己的同伴,而她另一只眼睛直视我们。同伴看起来很放松,双手放在头后面,慵懒怠惰。她的黑头发梳理得无可挑剔,整齐地落在床边,虽然用的似乎是耙子而不是梳子。条纹床垫倾斜、旋转,仿佛要完全翻转过来,让我们能对这裸体一览无余,眼光游走,随着她身体的曲线和反曲线。
床看着不太舒服,它的床罩太薄、太硬。总的来说,它与女人明显的安乐情绪不协调。人们会想起囚徒的稻草垫子,而不是滋长未来激情的温床。
时值1942,这一年德国占领了巴黎。过低的屋檐下,能感受到空气不足。水泥的颜色覆盖了从灰色到黑色、再从黑色到各种灰色阴影的范围。阴影逐渐缩小到一个点。在它的角落里,这个房间没有想好是要提供保护,还是要展现威胁。各个角落掏出一个空间,或者可以说它们闭关自守,向内投射,冲向房间内的人。房间内部扭曲,就像一个因为外力变形的纸板盒子。女人尖尖的头和乐器一起,两个角度构成某种怪异的和谐。这些只是看上去巧合,支离破碎的人物背后是另一种逻辑。
人物们看起来被打成了碎片,而且有人试着要把她们拼在一起,却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做。他们很着急,却无法回忆起这些碎片是怎么放在一起的,而且同样无法找到所有丢失的部分。有些可能滑到一边去了,要不然就是被重击完全粉碎。而且,还有人在看着,所以速度十分重要。她们的姿势必须摆好,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其结果,就是冷静和混乱的古怪混合。世界错位了,不过其中的一切都还能认出来。
我们回想起平静的时光,至少回想起某些特定时刻。一瞥,仅仅是一些琐事,微不足道的事情。就像历史本身,照片都被撕碎了,只剩下碎片,这些碎片还能重新粘贴回去,只是不完美。不再有什么延续感,无法把一个事件接续另一个事件;所有这些无足轻重的时刻,我们感受到它们在我们指间滑过,没有哪个还能持久。一种紧迫感打破了这段思绪。所有现实的碎片都已获得同等重要性,每一片都比以前更有价值。它们可以证明保存下来的东西。
对于晨歌来说,这是奇怪的时间和地点。标题让人回想起悠久的传统,从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画派,延伸到19世纪的安格尔,他们全都赞扬视觉与音乐之美的联姻,将身体的曲线与悠扬婉转的旋律结合在一起。从伊斯兰闺房中的神秘,到奥林匹斯山的壮伟,宫女和爱的女神们慵懒倦怠,聆听着总是与她们的身体呼应的音乐。她们是欲望的图景,存在于以艺术与爱为永恒法律的世界。
人们会想:这些已经没剩下多少了。毕加索笔下那拼凑在一起、斜倚着的女人,很容易让人产生讽刺感。另一个任务,她也不大可能冒险弹奏乐器,因为上面没有弦,也就变成了有讽刺意味的存在。
曾经用来表达完美之美的主题,为什么现在要用一幅画虐待它?而且,在这个恐怖时期,一个人怎么还能清晰观察这样的一个世界?正确的比例已经失去。对于如何使用美的指示也都被抛在一边。现实如此骇人听闻,我们怎能接受历史的停滞?为什么一个人不能用尽所有力气,去会想这种美,即使结果只不过是它扭曲的遗迹?
构成这些女人的元素可能来自不同人。一个艺术家用这种方式作画,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期画家,特别是古代经典画家们,常常从不同模特身上选取最好的部分,以创造出完美的、自然界不可能存在的图像。他们会用一个人的体型,另一个人背部的一块儿,第三个人的脸,等等等等。这种方式产生的雕塑或人体,就像某种纲要,不同部分的集合,聚集在一起,创造出理想化的印象效果。
毕加索笔下的身体表现出异质性,会让人以为他也采用了同样方式,有意强调他的模特迥然不同的特质。他使用古典手法的个人方式,变成了对于回收的歉意。他画出的,是一个回收过的裸体。评判标准不再是绝对的美,甚至跟美没有关系,只是存在,如此而已。
毕加索什么都没有破坏。多亏他,他的人物保持住姿势,等待更好的时间,似乎进入沉思。毕加索帮助她们坚持。他赋予她们生命,为希望伸出援手。而且,握住曼陀铃的手举起的方式,让人很难说它到底属于谁:是女人的左手,还是画家的右手?画作将碎片放在一起。它的人物适应了困惑的现实,表现出合作的态度。地上有一个空空的画框。有些画逃走了,其它的会过来。
曼陀铃的演奏者坐着,身体侧向椅子一边,她的脚底是灰色软毛毡。她的肚皮上有鸟的轮廓。她裙子的颜色通常是哀悼时用的:我们这里看到的场景有某种仪式感和庄严感。但是她的头发是绿色的,脸完全是蓝色的。生命激动人心。自然已经就绪。田野不远,天也是。这幅画让人看到未来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