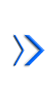三、中法文化交流的初次高潮
[西学东渐]西欧传教士来华的主要活动是传教。但这些传教士本身大多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因此,当他们在传教的同时,把西方的书籍、科学仪器带到中国,把西方的科学文化介绍到中国。这就揭开了西学东渐新的一页。其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早在1620年,法籍传教士金尼阁,在第二次来华时,带来了教皇保罗五世颁赐的7000余部书籍,书运抵澳门,后陆续运往京城,是否全部运入,尚存疑问。据载,7000多部书,选择精良,“重复者不入,纤细者不入”。除了神学、哲学书籍外,还包括数学、物理学以及其他科学类书籍。以后欧洲传教士将某些书译出,第一部译著是由比利时人邓玉函和王徵合译的《远西奇器图说》。
自路易十四派遣第一批法国传教士来华以后,在华的法国传教士陆续增加。他们传播西方科技与文化,努力为朝廷服务,以取得中国政府的信任。
时值中国清代康熙皇帝在位时期,康熙对西方文化采取开明态度,自己也专心学习。为了学习西洋科学,最初请比利时人南怀仁为师。南怀仁死后,康熙又召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进内廷,供奉皇帝学习西学。传教士每天早上4时到廷,日落而归,上下午给皇帝各上2小时的课,讲授西方数学、哲学、天文学、历法以及炮术实地演习等课,历时四五年。
除了服务于宫廷外,他们还通过翻译、著述,实际工作等,把当时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带到中国。
在舆地学上,法国传教士的最大贡献是绘制《皇舆全览图》。1708年(康熙47年),皇帝命传教士分赴蒙古和内地,绘制一幅较为详细的全国地图。
担负这项工作的主要是法国传教士,参加测量调查的有法国人张诚、白晋、雷孝思、杜德美、冯秉正、德玛诺等,还有一名日耳曼人和中国学者何国栋。
他们采用西方先进的科学仪器和绘制技术费时近十载,于1717年完成各省地图的绘制。最后由雷孝思、白晋等人汇成总图一幅。康熙命名为《皇舆全览图》,此图绘制精细,测量准确,是当时中国最科学的一幅全国地图。
在天文学上,法国传教士蒋友仁曾向中国皇帝介绍了哥白尼的日心说。
1757年,罗马教廷废除了对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禁令,西方传教士才正式把这种学说介绍给中国。1760年,蒋友仁借向乾隆皇帝献《坤舆全图》的机会,在地图的四周布置了天文学内容的插图和文字说明,宣布哥白尼学说的正确性。此外,法国遣使会士罗广祥曾在钦天监任职。
在算学上,杜德美输入割圆术。杜德美将割圆术授给满人明安图,明安图于乾隆初年始编《割圆密率捷法》一书。
在建筑方面,圆明园的畅春园仿法国宫殿而建,是乾隆委任法国传教士蒋友仁等设计的,其中谐奇趣、蓄水楼、花园、蓄雀笼、方外观、竹亭等十二处的喷水池和白石雕刻,全部模仿路易十四时代的风格。
在语言学上,法籍教士金尼阁著有《西儒耳目资》三卷。首卷为文字学及概述;中卷是依音韵排列汉字;末卷是以字偏旁排列汉字,并以西方字母为其拼音。主要为西方人攻读汉文的工具书,但在音韵学上也是有价值的。
[中国文化在法国的介绍]法国传教士一方面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又通过记叙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介绍中国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科学成果以及翻译中国典籍,把中国的古老文化介绍到西方和法国。
法国传教士从十八世纪初到十九世纪初出版了三部巨著,介绍中国科学与文化。
(1)《海外传教耶稣会士书简集》1702—1773年陆续出版,共34卷,其中第16—26卷是关于中国的。这部书汇集了当时传教士们从中国寄回欧洲的书信,对中国情况有详细描述。
(2)《中华帝国全志》由竺赫德主编并作序,1735年出版,共4卷。此书收集了传教士发自中国的回忆录,记述中国地理、历史、年代、自然情况,附有64幅插图,其中50幅是地图和城市简图,14幅风景、服饰等等的插图。
(3)《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人的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等论丛》简称《中国论丛》,1776—1814年出版,共16卷。
此外,法国传教士宋君荣、马若瑟等把中国古典经籍,如诗、书、易、礼译成法文,并加以注释。冯秉正依据朱熹的《通鉴纲目》编译成法文,题名《中国通史》。宋君荣还把诗经、书经上的天文历算,摘译成《中国天文历史》,把《成吉思汗》、《蒙古史》也译成法文。法国人殷弘绪、赫苍壁等将朱熹的《劝学篇》、刘向的《列女传》、《诗经选篇》译成外文,还翻译了中国的《养蚕术》、《图注脉诀辨真》、《泉币志》等。
如此大量的有关中国的文献传入法国,引起了法国思想界的极大关注和浓厚兴趣,尤其在启蒙思想家中反响非凡。
当时法国封建专制制度已陷入深刻危机中,新兴资产阶级力量正在壮大,作为革命先驱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应运而生,启蒙思想家用“理性”的武器无情地批判现存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同时他们也需要得到新的思想材料、新的治国蓝图来丰富充实自己的理论,来设计未来的新社会。而这时经过传教士的滤色镜而传入法国的中国文化正好适应了启蒙思想家的这种需要。
耶稣会士对中国的介绍是经过他们主观加工的,难免有夸张和偏见。同时,启蒙思想家由于思想体系和思想方法的不同,对来自中国的文献材料也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中国文化对当时法国思想界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一部分思想家对中国文化赞扬备至,他们要奉中国文化为楷模,并用中国的事例,抨击天主教神学的迷信和黑暗,反对专制王权,宣扬信仰自由,宣传自然神论。其中著名的代表是伏尔泰、百科全书派和重农学派。
伏尔泰曾在许多著作中提到中国,赞美中国。在他的名著《各民族风俗论》中,中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他的《哲学辞典》和为《百科全书》撰写的一些条目中,对中国的历史、哲学、政治制度、道德宗教观、教育都推崇备至。他还把元曲《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剧本。在《路易十四时代》的最后一章关于中国的“礼仪之争”中,对中国也不乏赞美之词。
伏尔泰赞扬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在他写的《百科全书》 “历史”条目中写道:“使中国人能立于世界各民族之上的,就是他们的法律、他们的风俗,他们读书人所讲的语言约四千年未曾改变。”该民族“在我们认识它的某些个人之前就已创造了几乎所有的艺术。”在《哲学辞典》 “光荣”条目中,他更是坚持了这样的观点:“世界历史自中国始。”伏尔泰还竭力推崇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在《哲学辞典》“中国”条目中,他写道“他们帝国的政治制度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只有它是完全建筑在人权之上的,只有在此制度下,一个省的长官如果不受人民的欢迎,就会被撤职,受到惩罚;⋯⋯。”他还指出:“中国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伏尔泰还根据儒学合道德和宗教为一身的特征,把它认定为自然神论,以充实自己的宗教理论,他认为儒学是具有崇高理性、合乎自然和道德的新“理性宗教”,他用它来反对欧洲当时盛行的基于迷信的“神示宗教”。他认为“孔子使世人获得对神的最纯真的认识。”这就是唯以德教人,要求人们修身、治国,都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理性,“而无需求助于神的启示。”他认为,在人之间存在一条基本的不朽的规律,这就是“己所勿欲,勿施予人。”他公开号召欧洲向中国学习:“当欧洲的王公贵族听说这样的榜样时,该怎么办?敬仰和羞愧,但更重要的是仿效。”
“百科全书”派对中国的看法和伏尔泰相似,狄德罗夸奖儒教,“只需以理性或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霍尔巴哈主张象中国那样以德治国,他使用了“德治”一词。在《社会体系》一书中公然宣称:“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爱尔维修在《论精神》中也有类似的溢美之词。波瓦伏尔在 《哲学家游记》中,更表现出对中国的盲目崇拜。他写道:“如果中华帝国的法律成了各国的法律,那么世界将会成为什么样子,中国提供了这样一幅诱人的图景。到北京去!去瞻仰世上的最强者,那才是上天真正完备的形象。”
重农学派对中国的看法不仅仅停留在赞美上,而是用中国的哲学政治思想来充实自己的理论,真正从中国的文化中汲取营养。这个学派主张以“自然法则”和“自然秩序”替代上帝的神示。它的创始人魁奈,因为推崇孔子学说,有“欧洲的孔夫子”之称。他认为,“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但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是例外。”
他根据中国理想君主无为而治的思想提出,一旦君主依自然法则改革了立法,他就不须干任何事,“让法律来统治。”重农学派学说的重心在经济学说上,他们认为,所有的财富来自于土地的产品(如农业、采矿、伐木)。
这种重农思想,也可以见到中国以农为本思想的痕迹。魁奈非常赞赏中国的重农主义和历代君主重视农业的政策,在他充任御医时,曾鼓动法王路易十五在1765年仿效中国皇帝举行春耕“籍田”仪式。另外,魁奈关于实行土地单一税政策的主张,也出于中国古代税制,特别是受《周礼》均田贡赋法的启示。重农学派在教育学上,提倡教育世俗化和教育普及。在这方面也受到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在他们眼里中国人通过读书科举便可进入仕途,不受贫富和宗教的限止。魁奈认为,公共福利必须依赖于对“自然秩序”的学习,在这方面唯一在中国引起重视。中国古代思想和政治制度对重农学派政治思想和经济学说的形成,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当然,也有一部分思想家,例如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是从消极面来看待和总结中国文化的。
孟德斯鸠为了论证他三权分立的政治理论和实行开明君主制的理想,他把世界上的政体分为三种,即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把中国作为专制政体的典型。他通过对中国的大量研究,表示出和伏尔泰截然相反的态度,对中国的美好描写以示怀疑,而对中国君主暴戾、中国的丑陋现象的描写却深信不疑。
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论述散见于许多著作中,如《论法的精神》、《思想》、 《波斯人信札》、《随笔》、《地理》和《论一般专制政体》,其中《论法的精神》全书31章中,提及中国的多达21章。在孟德斯鸠笔下,中国是暴戾的专制国家。他说:“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他认为,中国的君主集宗教与世俗大权于一身,对臣民实行独裁统治。中国的刑罚残酷,炮烙、凌迟等酷刑令人发指,而且往往株连九族。他认为,中国人口奇多,耕地不足,人民生活贫困,弃婴到处可见。因此,他认为,中国不能成为欧洲的模范。
卢梭是主张主权在民的民主主义者,所以他对一切君主政体都深恶痛绝,对中国的专制统治也不例外,他在《科学艺术论》一书中,对中国有许多非难之词。他用中国人文化进步,反丧失其民族牺牲精神,因而不能抵御蒙满的入侵一事,来为自己的学说服务。他指出:“如果科学真的使道德净化了,科学教导人们为祖国而流血,科学给人以勇气,那么中国人必然是智慧的、自由的、不可战胜的⋯⋯但如果中国大臣们的能力,中国法律所谓的明智,以及众多的中国居民不能保卫自己的领地,而臣属于无知的、粗暴的蛮族,所有这些聪明的人又有何用?”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在法国思想界引起不同反响,就是中法文化交流深入的明证。
[中国艺术和罗科科风格]17、18世纪的法国正是欧洲文艺、美术、戏剧、礼节、服饰、装璜仿效的中心。在路易十四时代,和专制王权加强相适应,法国和欧洲在艺术上盛行巴洛克风尚,其特征是富丽堂皇、庄严雄伟,但不免刻板和形式化。路易十四死后,人们普遍要求在各方面都摆脱专制王权束缚,和哲学思想的启蒙运动相呼应,在艺术上也倡导个性解放,摆脱古典的、呆板的艺术形式,于是,一种新的艺术风格——罗科科风格应运而生。如果说,巴洛克风格导源于古罗马的遗风,那么,罗科科风格实借鉴了中国艺术。
罗科科艺术风格的特点是明快、轻灵、生动、自然,保留有幽雅、精致、纤巧的中国艺术对它影响的遗痕。罗科科艺术风格的形成最初得益于中国艺术品流入法国。随着中法贸易的发展,中国的丝织品、瓷器、漆器等源源不断进入法国,法国的宫廷和王公贵族争相购藏中国物品。中国物品以其质地优良、装饰新奇而风靡法国,以致供不应求。因此,当时法国一些工匠开始仿效中国艺术品,以迎合法国人的“中国趣味”,这种对中国艺术品样式和装饰的模仿,最终旁及至绘画和建筑。从而促进了罗科科风格的形成。
瓷器在15世纪的欧洲还是稀有珍品。自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开始输入中国瓷器;17世纪以后荷英也参加了远东贸易。法国最早购买瓷器通过这些国家,“昂菲德里特”号商船首航中国后,才从中国直接输入瓷器。瓷器初入法国,法国人就用1610年巴黎流行的杜尔夫的小说《牧羊女爱丝坦莱》的情人赛拉同来称呼青瓷,因为赛拉同常穿青斗蓬。法王路易十四曾命令首相马扎然创办中国公司,到广东订造标有法国甲胄纹章的瓷器,凡尔赛宫内列有专室,供法王珍藏华瓷。法王路易十五曾下令,将法国所有银器熔化,以充国用,而以瓷器取代。18世纪后期,法国开始仿制瓷器,1673年在鲁昂, 1695年在圣克卢,都生产过黄色而透明的软瓷,产品是以福建白瓷为标本的。法国制造瓷器,曾得到景德镇神父殷宏绪的帮助。他在1717年将景德镇高岭土的标本寄往法国。1750年,杜尔列昂斯公爵下令在法国勘察瓷土。1768年在里摩日发现瓷土层后,塞夫勒瓷厂造出了硬质瓷器。
法国人在仿效中国漆器上略胜一筹。在路易十四时代,梅特纳夫曾在凡尔赛宫和特里亚纳宫中采用整套中国漆制家具。“昂菲德里特”号第二次来华带回了一批漆器,漆器才开始大量输入法国。不久,一些工匠就开始仿照中国式样制造漆器。最早是在法国圣安托万地区,以后以马丹家族的作品最为出名。马丹家族中有四兄弟都精以此业,而获得最大成功的是罗伯特·马丹。他的作品在黑色的底子上配有优美的花鸟图案。他特别得到了蓬巴杜夫人的欣赏。1752年,为了装饰她的贝勒维宫的需要,蓬巴杜向马丹订购了一大批漆器。马丹的名声超出了国界,菲特烈大帝把他的儿子作为漆工带到了普鲁士的宫廷中。
漆器不只局限于家具,中国的轿子也传到了法国。轿子在17世纪初便传入欧洲,1644年在法国文献中已见记载,莫里哀在多部喜剧中都提到过轿子,尤其是1659年的《风流妇女》,在路易十四时代,轿子作为东方等级社会的象征也在法国流行,和当时的专制主义相适应。以后法国人把轿子改为装上轮子的轿式马车。路易十四以后,轿子在法国逐渐减少,而轿式马车开始流行。在1737年,只有老百姓还使用轿子,而富人都坐马车了。但是这种马车在材料和式样上还保留了轿子的痕迹。
17、18世纪,尽管欧洲早已能自己生产丝绸,但由于中国丝绸价廉物美而深受欧洲人的青睐,进口量大大增加。这时,中国的丝绸,欧洲的仿制品,以及中国的棉织品被广泛地用于服装、悬物、被面等。蓬巴杜夫人就曾穿用中国花鸟的绸裙。作为丝绸的附属物,中国丝绣也促使了法国刺绣的变化和多样化。皮尔蒙的花卉设计图案明显受中国样板的影响,他曾长期在里昂居住。丹尼艾尔·马罗的制绣图,大胆地把螺旋形、格状形和自然的小花结合在一起,和中国的刺绣十分相似。
此时,中国的画屏和壁纸在法国也成了时尚。欧洲在16世纪就能生产壁纸了。但是壁纸的广泛使用和中国样式壁纸的生产也是自18世纪中国壁纸大量进口时起。当时中国壁纸单张高12英尺,宽4英尺,每套有一系列关联的图案构成,可以糊满整个房间。图案起先多花鸟,后期增加了山水、人物、种茶、制陶的场景。1688年,法国仿中国壁纸制造成功。
瓷器、漆器、彩丝、画屏等最初并不是作为精美的艺术品,而是作为质量上乘的生活用品而输入法国的。但是接着出现了追求中国趣味的风尚,中国的样式和设计原则为法国人所熟悉。中国物品装饰的图案和图案表现出来的新世界影响了法国人的艺术追求,于是在艺术领域,如绘画、建筑、园林等方面,成为罗科科风格兴起的重要来源之一。
在建筑上,当时法国主要的大建筑物几乎没受罗科科风格的影响,古典传统还是占支配地位,但在一些小的建筑物,尤其在乡村别墅和避暑庄园上,体现出罗科科风格的痕迹。法国罗科科的典型建筑是1722年完成的桑梯里小城堡亲王厅和巴黎苏毕士旅馆的“沙龙”,构造的轻巧,屋顶多取圆弧而避方尖,奇异的尖顶饰、屋檐下的挂钟、游廊、方格窗等是罗科科建筑的典型特征。中国园囿建筑,在英国发展最盛,后来传至法国,称为“中英式花园”,法国香德庐正是一例。
在绘画上,罗科科风格代表首推华多,他的作品常以浅色表现,黯淡的流云和纯朴的山景构成画面烟雾迷濛的韵致。有人认为华多的画极似中国宋代之风景画,他的作品《孤岛帆阴》,被公认为具有中国风格的佳作。
罗科科风格延续了几十年,1755年随着庞培城的考古发现,新古典主义兴起,约在1780年,罗科科风格被新古典主义所取代。
17、18世纪中法文化交流的发展是中法关系史上光辉的一页。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产生了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政治哲学,中国也逐渐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此后,中国在法国人心目中的形象逐渐淡漠,中法间一度的亲密接触又疏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