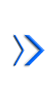一、1800 年以后的激进主义运动
秘密结社活动 1799年7月,议会通过“结社法”,指名取缔了“伦敦通讯会社”等群众组织,议会改革运动受到沉重打击。这以后,一切合法活动都“非法”了,英国进入恐怖而黑暗的时代,90年代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停止了,化为细水流入地下。19世纪最初10年的人民运动,就是以地下斗争的形式出现的。
结社法公布后,“伦敦通讯会社”并没有停止活动,至少在1800年11月,人们还能看到它暗中活动的迹象。“联合爱尔兰人”和“联合英格兰人”
隐蔽得更深了,更难发现他们的踪迹。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组织,分布在北、中部广阔的工业区里,秘密地进行活动。据地方官报告:1801年,约克郡西区的许多工业城镇发现有地下活动,特别是当年工人运动的中心设菲尔德,秘密会议极为频繁。《里兹信使报》也报导类似的集会在利兹附近相当多。1802年,还发现一份8页纸的传单,号召人民组织起来,推翻暴政。同年秋,两个设菲尔德人被交付审判,罪名是“非法起誓”。据说他们参加了一个秘密组织,该组织有1000多人,正在打造武器准备起事。各地组织间还有经常的联系,据兰开郡地方官说,1801年1月该郡曾召开一次秘密代表会议,伦敦、伯明翰、布里斯托尔和约克郡许多地方都有人参加。7月,约克郡的哈里法克斯也开过一次代表会议,参加者来自许多纺织市镇,还有设菲尔德的代表。与会者必须回答3个问题,其中第一个就是:是否应当改变现存的制度?
由于处于地下,组织的安全就成了头等大事。因此,这些组织一般都比较严密,有严格的纪律。特别是在吸收新会员时,更加显得谨慎。新会员入会须有可靠人介绍,且经过一定的考察;入会要履行手续,主要是进行宣誓。
1801年,博尔顿有一个叫“议会改革政治同盟”的秘密组织,它的誓词说: “我自愿宣誓,为争取全体英国人的友好相处,不分宗教信仰;为争取全国人民的平等代表权,我将努力奋斗,坚持到底;为履行以上职责,我要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永不背弃本会或兄弟协会的任何成员。无论是有意无意,直接间接,都不泄漏他们的一言一行,也决不提供不利于他们的任何证据。”许多组织在宣誓时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如悬挂死神像、念符咒、歃血为盟等等。有些组织要求当着死神像宣誓严守机密,永不叛离,一旦泄漏组织秘密,愿意接受死的制裁。凡此种种,不仅使局外人觉得神秘莫测,就连宣过誓的会员,也时时感到一种死的恐怖在笼罩着,因此,绝不敢轻易吐露真言。由于组织非法,其活动也就隐秘异常,往往是聚无影,散无踪,昼伏夜出,深更半夜在荒山野地里聚会议事。1802年有一个叫“黑灯照”的组织在里兹一带活动。里兹市长有一次写信给郡守报告说:这个组织“星期五晚上的子夜时分,在离利兹6英里、伯斯托尔4英里,远避一切交通要道的一段荒路或峡谷中开了一次会。一个诚实可靠的人告诉我说,他企图假扮成开会的人,但发现老远就有人把守。最外一道防线的人走过来搭讪,想把他引到不同方向去。他吵着要过去,这时他发现还有一道不固定的流动防线,他们问他是干什么的。当他继续向‘黑灯照’挤过去时,一声口哨响了,随即他听到人的说话声,其言词和声调使他决不敢向前再走出一步。”利兹市长接着说,他从其他情报来源得知,那天晚上集会的是“黑灯照”的总委员会,约200人,每个人又代表其他9个人。“‘取消一切赋税,享受全部权利’,就是头领们提出的口号,也是把他们连接在一起的共同纽带。到圣诞节时他们就能功成名就,某一天晚上他们会在各个地方同时举事。”与这封信几乎同时,伦敦收到了许多地方当局发出的武装起义警报。
1802年11月,政府逮捕了德斯帕德上校,说他阴谋推翻政府。德斯帕德出身于爱尔兰一个地主家庭,年轻时从军,在西印度群岛和英属洪都拉斯作过战。1790年他应召回国,从此断送了立军功的前程。不久,他投身于工人运动,参加了“伦敦通讯会社”,当选为总会代表。“伦敦通讯会社”被镇压后,他被关押两年而未加审判。1800年从狱中出来,他就开始紧张的活动,在伦敦工人中进行工作。他每天出入往返于工人聚集的下等酒吧间,与一群又一群工人、士兵会晤交谈。作为一个出身高贵的军官兼绅士,这是非同寻常的,因此他的举动受到严密的监视。政府指控他通过这些活动组织了一支革命军,仅在萨索克一地,就有7个“师”外加8个“旅”。这支革命军遍布伦敦所有工人区,工人是其中的主要力量。此外,他还策划兵变、推翻政府、逮捕或杀害国王。据此,政府对他提出起诉。但在审判过程中德斯帕德始终一言不发,只是在宣判死刑后,他才否认曾引诱过士兵,这使人觉得他仿佛是默认了密谋的存在,只不过从事策反工作的不是他。当他登上绞刑架时,他说:“我知道,由于敌视政府那些血腥、残酷、强制而又非法的手段,政府已决意拿我开刀,却又用他们津津乐道的法律作借口。公民们,祝你们健康、幸福、昌盛。虽说我不能活着体验那神圣的变化带来的幸福,然而请相信,公民们,那一天终会到来,而且会很快到来!”卢德运动秘密结社活动的最高潮是1811年—1812年的卢德运动。这个运动的细节至今我们知之甚少,只知道运动的地方性很强,从未发生过全国性行动。
但其组织性之强、活动方式之相似、步调之一致,又好像存在着统一领导,至少是地区性的联合委员会。参加运动的人昼伏夜出,在茫茫月色中,几十个人乃至数百人,头戴假面具,手执棍棒武器,突然出现在某村某镇,专与欺压工人最甚的老板作对,捣毁他们的设备,破坏违反行业生产规程的机器,对严格遵守行业规定的厂商和织机又严加保护。行动完毕,一声令下,就悄然散去。这些说明卢德运动是相当有组织的行动,他们事先对一切行动都作过最严密的规划。他们声称自己受“卢德将军”管辖,各地区都有他的一名代表——“上尉”在具体负责。至于“卢德将军”是谁,或者有没有这个人,直到现在都还是个谜。卢德派和秘密结社的关系可从他们的誓词看出来。有一份卢德派誓词说:“我,某某,于此自愿起誓:我将永不泄漏本秘密委员会任何成员的姓名,否则将受惩罚,被第一个碰见我的兄弟送回老家;我并进一步起誓:如果出现叛徒,我将带着无尽的复仇心追踪他,哪怕他逃到天涯海角……”卢德派还有暗号和隐语,以便不同地区的卢德派彼此辨认。有一个记载说:“你必须把右手高举过右眼,假如有另一个卢德派在场,他将把左手高举过左眼……他会说:你是干啥的?回答:铁了心眼儿的。他会说:为啥?你回答:自由。然后他将和你说话,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
卢德运动发源于诺丁汉市。1811年3月11日,诺丁汉市的织袜工停止工作,在市中心商场举行群众集会。附近许多村镇的群众也赶来参加。当晚一批自称是“卢德将军麾下”的人乘夜色潜入阿诺德村,捣毁了一个顽固商人的60部袜机。这以后,运动就猝然爆发,迅速扩展,起先还只在诺丁汉市一带,随后扩大到整个诺丁汉郡。不久,又在德比和莱斯特郡蔓延开来,捣毁织袜机的行动几乎夜夜都有,整个织袜区一片动荡不安。当局出动了大批武装力量,仍无济于事。到第2年2月,总共捣毁织袜机约1000架。只是在多数袜商接受了工人条件,议会又通过镇压性条例,重判砸机罪以后,运动才突然停止。在兰开郡和约克郡,运动表现得更为激烈。兰开郡的手织工曾与雇主谈判,要求恢复工资。雇主起先答应,然后又反悔,在这种情况下,运动骤然而起。1812年3月20日,手织工开始袭击工厂,砸毁机器。以曼彻斯特为中心,附近几十个纺织村镇同时卷入运动,并成立了秘密委员会,统一协调行动。厂主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有一家工厂被围攻了3次,最终才被烧掉。4月20日,在米德尔顿的一次冲突中,厂方开枪打死5人,还有 10余人受伤。第二天,卢德派出动了好几百人放火烧了厂主的住房,这时,军队赶来镇压,又死伤多人。在约克郡,当卢德派围攻威廉·卡特莱特的工厂时,厂中守军和工贼开枪射击,重伤2人,后来这2人被卡特莱特抓去折磨至死。卢德派为报此仇,便企图暗杀卡特莱特,未遂,于是就枪杀了另一个与工人坚决作对的厂主霍斯福尔。这个案子到半年之后由于叛徒告密才得破案。1813年1月约克郡巡回法庭开庭,一次就处死17个卢德派分子,流放7人。正因为卢德运动如此激烈,哈孟德夫妇在写《技术工人》一书时,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时期的英国史读起来像是一部内战史。”卢德运动有时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在约克郡西区召开的一次代表会议上,一个名叫贝恩斯的老共和派分子说:运动的目标应该是“打倒嗜血的贵族”。他说:“我欢呼你们起来反对压迫者,希望它发展下去,直到世界上没有暴君为止。”他还说他“希望看到民主制度胜利的时刻。”1812年5月26日,曼彻斯特各业代表会议也通过决议说:“除了少数几个例外,我们名义上的议会代表……已不再是人民生命、财产和自由的忠实卫士了……希望唯一所在,就是赶快对下院进行有效的激进改革。”卢德运动为战后的工人激进运动提供了大量的干部和基本群众,从这个角度上说,它本身就具有政治意义。
等到拿破仑战争结束,议会改革运动重新兴起时,隐藏在地下的秘密结社突然涌出地面,劳动人民又成了改革运动的主力军。因此,19世纪最初15年的秘密结社活动,是两次人民运动高潮的纽带。
中等阶级议会改革运动在工人群众积聚力量,培养阶级意识的时候,中等阶级的议会改革运动也经历了一个重新组织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从1807年威斯敏斯特大选开始。1806年小皮特死后,由格伦维尔出面组成所谓“贤能内阁”,囊括了除皮特派以外的两党一切巨头,其中包括辉格党的福克斯和格雷。这使中等阶级改革派觉得有了一点希望。1807年,他们在威斯敏斯特全力投入大选,推举伯德特爵士和科克伦勋爵为激进派候选人,与托利和辉格两党对抗。但他们处境十分困难,普雷斯记载说:“我们没有钱,没法做宣传,没有人加入我们,托利党瞧不起我们,辉格党嘲弄我们。被人嘲笑才是最糟糕的呵……能经得起别人咒骂的人,经不起别人的嘲笑。”但选举结果却使人大吃一惊:两席全部被激进派赢去了。这次胜利使议会中出现一个新的激进派改革集团。为首的是乡绅伯德特,其他都出身于门第低微的市民阶层,如马多克斯是律师的儿子,纳普是杂货商。这样,议会在10年没有反对派之后,终于又出现一个吵吵嚷嚷的激进小集团。
这次胜利还有另一层意义。激进派能在一无后台二无钱的情况下夺取胜利,全靠竞选委员会的功劳。威斯敏斯特委员会存在了10年,为战后改革运动的蓬勃兴起准备了干部。伯德特、卡特莱特、科贝特、亨特、普雷斯这些后来在激进派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人,全都是委员会成员。
这一时期改革派的主要喉舌是威廉·科贝特。他在1802年还是政府的支持者,在陆军大臣温德姆的帮助下,创办了《政治纪事》报。但1804年他开始攻击政府腐败,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1806年他转向议会改革,此后《政治纪事》就一直是改革派的主要报纸。1807年,他参加威斯敏斯特委员会的工作,是这次竞选活动的主要宣传家。他利用威斯敏斯特选区工人阶级选民占优势的特点,直接向手工工匠进行宣传。正是由于他的宣传,改革派才取得工匠选民的普遍支持。
科贝特虽是宣传的大师,但行动的巨匠却是70年代的改革老将,《抉择》的作者约翰·卡特莱特上校。他在18世纪90年代显得不那么出众,但在19世纪初阴暗的日子里,当老一辈中等阶级激进派都对改革丧失信心时,只有他坚持不懈,为改革力量的重新组合作出了贡献。自1811年起,他以年逾古稀的高龄3次出游北、中部工业区,向工人传播他的改革福音。他曾坐着颠簸的邮车,在29天里行程900英里,所到之处都召集群众大会,一个月内在 35个地方讲演。他的本意是“把不满转到有利于议会改革的合法轨道上,”
从而阻止“煽动穷人侵犯富人财产的企图”,其结果却是复活了工人群众有组织的公开活动。1812年他和伯德特共同发起“伦敦汉普登俱乐部”,其纲领是“保证人民自由选举下院代表”和“改革下院代表制”。但这个组织贵族味太重,它的会员必须有300镑的财产资格,每年会费2几尼(2镑2先令)。卡特莱特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他曾写道:“在社会一大部分人眼中,它当然是个特殊的团体。”当时白色恐怖盛行,上中层人物对议会改革敬而远之,因此到1814年,只有3名会员经常参加活动;到1815年3月,只剩下卡特莱特一人。在这种情况下,卡特莱特只好转向工人群众,把改革的希望和未来寄托在工人身上。于是,他第二次、第三次出巡北、中部工业区,在劳动人民中大力发展俱乐部组织。因此,到战后俱乐部运动兴起时,这个运动已基本上成为劳动群众运动。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亨利·亨特,这是位小康农家出身的改革派,体格雄伟,声音宏亮,说话很有鼓动性,是名噪一时的演说家。由于他在战后许多重要场合充当演讲人的角色,因而获得了“雄辩者亨特”的美名。在所有激进派领袖中,他最接近劳动人民,思想也最和他们相通,因此,观点也最激进。他的口号是“要么普选权——要么什么都不要!”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人民的不满又汇成一股群众运动的洪流。活跃在这一运动中的中等阶级主要是上面提到的那些人。至于辉格党,他们在整整20年中悲观失望,游离于运动之外,甚至连改革都不敢提,深怕会把党内最后几个大贵族吓跑。他们把自己上台的希望寄托在威尔士亲王身上,认为“仅有的一点微弱希望在朝廷,即朝政易手的时候”。1806年他们参加“贤能内阁”,福克斯是最主要的阁员。但这届内阁根本未把议会改革提上议事日程,辜负了许多人满腔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