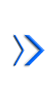二、议会改革运动的复苏
改革力量的集结 19世纪20年代,争取改革的力量经历了集结、改组的过程。
首先是辉格党在议会恢复活动,他们在“王后事件”中受到了鼓舞,重新把议会改革作为自己的口号。1820年初,辉格党领袖格雷伯爵还在悲观地说,在他有生之年将不能看到议会改革了,因此不必为此操劳太多,但1821年1月,他已经把“完全彻底地改变政府体制”视为己任。1822年4月,罗素勋爵在议会提出改革动议,要求把100个衰败选邑的席位各减去一席,分给郡选区和没有议员选派权的大城镇。这项动议以164∶269票失利,但这是1785年以来获得支持最多的一项改革动议。1823年罗素再次动议改革,但成绩远不如上一年好,接下来的两年辉格党毫无作为,好像对改革失去了信心。1826年,辉格党对大选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指控,逼迫议会剥夺了东雷特福和彭林两个镇的选邑权。但当罗素提出要把这两个镇的席位转给曼彻斯特和伯明翰时,却受到托利党贵族的强烈反对,议会为此辩论了3年,结果还是把这些议席转到附近农村去了,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的工业家在希望完全破灭后,带着一腔怒火投入改革。
工业资产阶级在此之前很少投身议会改革,他们或者游离在改革外,或者站在政府一边反对改革。“彼得卢事件”中参与屠杀工人改革派的主要就是曼彻斯特资产阶级子弟组成的义勇骑兵队。但东雷特福—彭林事件后,工业资产阶级大量转向改革。1832年工业家弗赖尔说的一段话颇能说明这一问题: 50年前我们不需要议会代表,现在我们需要了。因为那时我们几乎完全为国内消费而生产,商业区和工业区是合而为一的,一荣俱荣。现在却大不相同了— —我们现在为整个世界生产,假如我们没有自己的议员来促进和扩大我们的贸易,我国商业的伟大纪元就结束了。工业资产阶级运动的中心是英国黑色金属工业的心脏伯明翰;它的领袖人物是托马斯·阿特伍德。伯明翰是个小企业林立的地区,迟至1843年,当地大部分工厂也还只雇用6、7人至30人不等。由于企业小,老板略遇风浪就破产,帮工稍聚几文便开店,因而阶级分化不明显。1829年经济萧条,伯明翰受到沉重打击。5月8日,在一次地方性会议上,阿特伍德花了3小时宣讲币制改革,然后通过一项决议,送交议会。但政府很快就退回了请愿书,谈吐中还不乏轻蔑之辞,这大大触怒了伯明翰的工业家。于是,阿特伍德这个在1825年还发誓“不和激进派来往”的人,一夜间竟成了激进改革派。1830年1月25日,他发起成立了改革斗争中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政治组织——“伯明翰政治同盟”。它的成立宣言说:大贵族在下院有充分的代表权……工业和商业却几乎全无代表!它们是国家最重要的利益所在,是国家财富与力量的源泉,相比之下它们代表不足,而和国家的累赘(指贵族)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每一项利益,却被代表得足而又足!因此,改革这种状况对国家的昌盛极为重要。一般来说,下院中“市镇公民”的代表应该是真正的“市镇公民”,即经营实业,积极关心它,将其毕生的财产与幸福委托于它的人。由于伯明翰阶级分化不明显,同盟的基本群众是工人和工匠,因而声势特别大。尽管如此,它仍不失是纯粹资产阶级性质的组织。同盟的6个创始人,阿特伍德是银行家;斯科菲尔德是银行家兼工业家,伯明翰的头号巨富;琼斯是金银器兼纪念章制造商;索尔特是灯具制造商;哈德利是钮扣制造商;芒茨开金属辗轧厂。此外,当地辉格党首脑,后来成为同盟二号人物的约瑟夫·帕克斯,是大厂主的儿子,本人是律师。同盟政治委员会的36名委员会中,有蒸汽机制造商、制绳商、铸铜商、商店老板、律师、小学校长等等,只有一个工人,其阶级性质由此可见一斑。
除工业资产阶级外,“中等阶级”还有另一个阶层,这就是工业革命前就已存在的“旧”中等阶级。他们是商人、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等。正是他们最早形成群众性的议会改革运动,而且长期以来发挥着重要作用。
18世纪60年代的威尔克斯事件和80年代的“宪法知识协会”都是他们活动的结果。法国大革命时他们也曾投入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19世纪初,他们的活动陷于消沉,但20年代末又开始重新复活。1830年3月8日,伦敦成立“首都政治同盟”,表明“旧”中等阶级又有了自己的组织。
和中等阶级一样,这时工人阶级也可分为两个阶层:一个是工业革命前就有的手工工人阶层;一个是工业革命所造就的工厂工人阶层。工厂工人受欧文的影响相当深,多尔蒂就自称是欧文主义者。建筑工会领袖莫里森曾写信给欧文说:“我希望您将毫不迟疑地指出我的错误、偏见和天生的弱点。
您的学说使我成为更完善更幸福的人……”但欧文是反对改革的,他说即使实行了普选制,“也不会给工人阶级带来多大好处,甚至根本不会有好处。”
因此在他的影响下,工会运动和其他产业工人运动都偏重经济斗争,对议会改革兴趣不大。尽管如此,工会组织对议会改革仍持积极的态度,比如1831年3月5日,辉格党政府提出改革法案的第5天,多尔蒂创办的《人民之声报》就表态说:“尽管法案具有较强的人民性,超出我们对现政府的期望,但仍然没有一项条文……是为工人利益制定的。……然而人们将从选邑贩子们那里取得某种东西,假如法案不夭折……通向其他更有用的改革的路就筑起了。”6月18日,多尔蒂更明确地说:“法案是通向我们的目标——建立普遍的政治自由——的辉煌的一步。”手工工人则有悠久的政治斗争传统,为争取普选权而长期斗争过。法国大革命时期他们掀起过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伦敦通讯会社”就是他们的组织。19世纪初,当辉格党贵族和中等阶级改革派都销声匿迹、意气消沉时,只有他们仍然坚持斗争,把运动推向高潮。但他们对议会改革的态度是:要么普选,要么什么都不要。因此他们在1830年—1832年的改革高潮中坚决反对辉格党政府的提案,认为这是对改革事业的背叛。他们要求实行彻底的成年男子普选权,实际上是要求工人阶级选举权。他们的态度后来在争取改革的斗争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在下文将会谈到。1830年5月,伦敦手工工匠成立“工人阶级全国同盟”。这是在改革斗争中最重要的一个手工工人政治组织,它自称与外省104个类似的组织有直接联系。
就在改革势力积聚力量的同时,反改革阵营却在剧烈分化。20年代初,托利党自由派实行某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党内保守派对此始终耿耿于怀,因此托利党内部的斗争愈演愈烈。保守派利用他们控制的地方势力暗中排斥自由派,比如1826年大选,自由派的重要人物、陆军大臣帕麦斯顿子爵突然发现他稳坐了14年的剑桥大学议席受到威胁,当地托利党在某些内阁成员的支持下准备把他轰下台,于是他不得不投靠辉格党以取得支持,这样才保住了席位。帕麦斯顿忿忿地说:“这是我和托利党分手的决定性的一步,而他们是侵犯者。” 1827年,首相利物浦中风,乔治四世不得已任命坎宁组阁,使斗争更趋尖锐。托利党长期以来在爱尔兰问题上观点不一,一派主张解除对天主教的宗教歧视,恢复他们的政治权力;另一派则主张维护国教的“独尊”地位,继续实行歧视政策。自由托利党人除皮尔外,都是解放天主教徒的坚定鼓吹者。尽管如此,坎宁组阁时,仍遵守党内惯例,不准备提出天主教问题。但以威灵顿公爵为首的党内保守派决心不让自由派组阁。他们以坎宁支持天主教解放为借口,一致退出内阁,以为这样就能整垮坎宁。坎宁为摆脱困境,不得已与兰斯多恩派辉格党结成联盟,联合组阁。在这次事件中,皮尔也站到了保守派的行列。此后,托利党自由派便称坎宁派。坎宁死后,联合内阁垮台,威灵顿出面组织清一色的托利党政府,但托利党内的分歧已不可弥合。
1828年5月,坎宁派在东雷特福议席转让问题上投票反对政府,主张让伯明翰获得议席。随后,哈斯基森率坎宁派离开内阁。至此,他们除议会改革外,几乎在一切问题上都和辉格党一致。经过10年的演变,托利党左翼终于分化出来。
随后,辉格党也开始重新集结。1830年3月开始,各派就在消除分歧。
4月,隐退10年的格雷伯爵终于出山,到伦敦考察局势。他认为当时的形势很像大革命前的法国:人民情绪激昂,政府软弱无力,若不及早采取措施,英国的贵族将与腐朽的制度同归于尽。格雷的复出使辉格党获得当然领袖,派系间争斗全然消除。接着,格雷决定与坎宁派结盟。经过几个月的谈判,制定出“和平、节俭、改革”的共同纲领,坎宁派终于在改革问题上也接受辉格党立场。不久,帕麦斯顿代表坎宁派通知威灵顿政府:他们“将投票支持”议会改革。至此,改革力量的集结全部完成。
这样,经过10年的集结、分化、改组,到1830年时,全国三大阶级6股政治力量中,只有托利党一小撮最顽固的保守派反对任何变革,其他各种力量都支持某种程度的议会改革。因此,从阶级力量对比看,议会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但托利党贵族仍掌握政权,而且有国王在暗中支持,所以,要取得改革的成功,还需进行一场艰苦的斗争。
天主教解放法改革的序幕是由“天主教解放法”拉开的。自英国征服爱尔兰后,爱尔兰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法国大革命时期,他们还举行过武装起义,企图摆脱英国的控制。1801年,英国通过“爱尔兰合并法”,用收买政策合并了爱尔兰议会,这以后,爱尔兰形同英国的殖民地。根据英国法律,天主教徒不能担任公职,也不能当选为议员,因此占爱尔兰人口绝大多数的天主教徒事实上成了二等公民,他们虽然可以有选举权,却不能选举天主教徒代表担任议员。这种政治上的歧视不仅为一般人民深恶痛绝,就连信仰天主教的中上层人士也大为不满。1823年,丹尼尔·奥康奈尔创立“天主教同盟”,受到全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支持,迅速成为当地最有号召力的政治势力。
1828年坎宁派退出内阁后,威灵顿指派菲茨杰拉德接任贸易大臣,菲氏是爱尔兰克莱尔郡的议员,根据法律,他必须在原选区补选一次。菲氏主张天主教解放,得到当地选民的支持。这本来不成问题,但政府自己把事情弄糟了。前面说过,天主教同盟此时已是爱尔兰最强大的政治势力,威灵顿对此十分不快。1828年6月10日,他在上院威胁要取缔天主教同盟,同时又声称:假如天主教同盟自行解散,政府“就有可能做点什么”来满足天主教徒的要求。这使天主教同盟处于两难境地:若解散吧,解放的事业当然就此告终;不解散呢,政府就可以说是天主教同盟妨碍了解放进程,因而为进行镇压提供了借口。威灵顿对自己的这一妙招十分得意,却没料到它把天主教同盟逼入绝境,迫使它背水一战。他们让自己的领袖奥康奈尔出面与菲茨杰拉德竞选,选举中动用了一切政治的、经济的、道义的力量,结果一举获胜,有史以来第一次选出了一位天主教徒出身的爱尔兰议员。
这次胜利使政府大吃一惊。他们害怕克莱尔选举会引起连锁反应:如果各地都选出天主教议员,那么虽说他们不能进入伦敦议会,却足以组成一个天主教的爱尔兰地方议会,爱尔兰的独立也就难以避免了。事实上,天主教同盟受这次胜利的鼓舞,斗志大增,正准备再接再励,夺取更大的胜利;爱尔兰的新教徒(主要是英格兰裔地主)害怕失去特权地位,则开始组织武装力量,打算进行反扑。内战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威灵顿政府不得不一反300年的基本国策,于1829年通过“天主教解放法”,以此为条件,解散了天主教同盟,保住了爱尔兰。
但“解放法”把火引到了托利党自己身上。党内反对天主教解放的极右派突然发现自己“被出卖了”,若不是“腐败的”议会制度通过了“解放法”,威灵顿决不能实现可耻的“背叛”!于是一大批“极端派”托利党人转向议会改革,托利党再次分裂。1829年6月2日,布兰福德侯爵破天荒以托利党人的身份提出一项改革案,将70年来几乎一切改革动议都集于一纸。这虽然有点滑稽,却表明政府已孤立无援,处于左右反对派的全面包围中,托利党的垮台指日可待了。
1830年7月,法国革命的消息传到英国,举国震惊。国内工人罢工,农业工人发动“斯文大尉”运动,更使得政局不稳。辉格党决定在此时提出改革问题,向托利党政府发动总攻。10月31日,辉格党决定由布鲁厄姆于11月16日在下院提出改革案。但不等提案提交,事态就发生急剧变化。11月2日,格雷在上院发言鼓吹改革,威灵顿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反对,宣称:我不仅不准备提出任何这种性质的方案,而且愿当场宣布:就我本人而言,只要我在国家政府中担任一官半职,我就认为我的职责是当其他人提出这类方案时进行抵抗。威灵顿发言刚结束,坐在他身旁的外交大臣阿伯丁就告诉他:“你宣告了你的政府的垮台。”果然,两星期后的11月15日,托利党极端派与辉格党、坎宁派一同投票击败政府。次日,威灵顿政府辞职,格雷伯爵受命组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