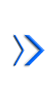三、1832 年改革
辉格党的改革方案 12月初,格雷授命达勒姆、罗素、格雷厄姆、邓坎农4人起草改革法。
据格雷厄姆后来回忆,当时他们从内阁得到的指示是:改革措施要“达到足以满足公众的舆论,为抵御进一步改革提供可靠保证,但又必须以财产为基础,以现有选举权和地域划分为基础,这样才不致冒破坏(现存)政府形式的风险。”人们对辉格党政府并不抱太大希望。近10年来,罗素是辉格党中最热衷改革的政治家,但他在几个月前提出的议案不过是把少数几个席位转给大城市,根本不涉及选举权问题。四人委员会中,只有达勒姆还稍稍得到激进派信任,但这也无济于事。更重要的是,格雷政府是历届政府中最贵族化的政府。内阁中除两个人外,所有大臣都是大土地贵族,或大贵族的儿子,而那两个不是贵族的阁员,仅格雷厄姆一人就有2.6万英亩土地。对这样一个政府,人们能期待些什么呢?因此,激进派冷眼旁观,不抱幻想;托利党则镇定自如,量格雷也不会走多远。
但3月1日政府公布草案时,却使全国大吃一惊。改革派欢欣鼓舞,保守派发誓要血战到底。政府到底提了个什么方案,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呢?它有3条原则:一是取消衰败选邑,把席位转给大城市和各郡。以1821年人口普查为据,居民数在2000人以下的 60个镇失去选邑资格,2000—4000人的 47个镇各失一个议席,这些议席分配给1万人以上而没有选邑权的大城镇,以及15万人以上的大郡县。二是扩大选举权,实行财产资格制。除原有选民外,在农村凡是年收入10镑以上的公簿持有农和50镑以上的租约农,城镇选区年值10镑以上的房产持有人均拥有选举权。三是减少议员总数,从658席减为595席。由此可见,这个提案的“中等阶级”性质很重,它基本上满足了中等阶级的要求。
辉格党之所以做如此大的改革,其目的格雷说得很清楚,是为了“把社会的中间阶层联合到上层中来,共同热爱并支持国家的制度和政府,这件事具有头等重要性。”为什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革命,只有避免革命才能拯救现存制度。辉格党是贵族,一方面要维持垄断政权的寡头制;另一方面,他们对它的弱点又知之甚深,知道它社会基础不雄厚,在财产和人数方面都很单薄。1830年事态发展更使他们深信革命形势已经形成,若不立即采取措施,一切都将在革命的狂飙中荡然无存。所幸的是,中等阶级虽已觉醒,劳动人民亦在骚动,但局势尚未发展到中下层人民结盟的地步,所以还没有爆发英国的“七月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树中等阶级为敌不如拉他们为友;一旦中等阶级自己得到满足,就会站在财产和秩序一边来,成为贵族制度的卫护士。出于这种信念,辉格党愿意主动后退,让中等阶级进驻自己的防线。正因为如此,格雷才说:“不做点什么是不可能的,但做得不足以满足公众期望……比什么都不做还要糟。”也正因为如此,才有政府对起草委员会的指示,也才有起草委员会的自白:“……满足一切合理的要求,同时立即并永远消除社会上有理智而独立的那部分人抱怨的理由。”其次,还必须考虑到辉格党自身的利益。罗素曾说过,假如改革后的议会提出的第一个动议就是再来一次改革,那么辉格党就失败了,就要垮台。
“假如按照我过去的计划,加顿和萨勒姆各保留一个席位,那么改革后议会的第一个议案,不就是拿掉这些地方余下的议席吗?”从这一点出发,辉格党认为他们的提案必须是“永久”的,至少经得住40年。在40年时间里贵族制不受新的威胁,辉格党就算坐稳了。
辉格党提案受到全国的普遍欢迎。一般老百姓都对议会辩论十分关心。
据记载说,人们往往在吃饭时捧着饭碗到街上打听消息,乡下人则步行几十里进城探问,或几个人合买一份报纸看。方案提出后,激进派领袖纷纷表态:伯明翰同盟于3月7日召开群众大会,向国王和议会发出贺信;亨特原则上表示支持;科贝特被政府指控为煽动农人暴乱,正在等候审判,但他也写文章赞扬法案,同时也指出它的不足;最后,正以分裂国家罪受到起诉的奥康奈尔也宣布赞成法案,使政府得到了爱尔兰的坚定支持。唯一反对法案的是伦敦的工人激进派,这在上文已经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1831年3月23日,法案以一票优势通过二读,从而进入小组委员会阶段。但4月20日托利党议员盖斯科因的一项修正案击败了政府,这预示法案在三读时可能失败。于是,在辉格党政府要求下,国王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
大选强烈地表现了人民的情绪。“法案、法案、完整的法案”这一口号提出来了,改革派到处胜利,反改革派纷纷失败。伦敦的4个议员中本来有一个反改革派,选举开始的第二天,他就被迫退出了竞选。多佛市头一天就选出两名改革派议员,当地长官威灵顿未能控制局势。索思沃克的改革派议员威尔逊支持改革法,但又投票赞成盖斯科因修正案,因此他虽然是格雷的挚友,却仍未能幸免于失败。盖斯科因本人更惨,他在利物浦市当选议员已 35年,这一次,选举开始仅10个小时,他就不得不认输。大选中托利党惨败,辉格党则控制了局势。英格兰40郡82席中,辉格党全胜的有35郡,托利党总共只得到6席。许多即将失去选邑权的村镇也选出了改革派议员,他们到议会来,唯一的使命就是投票取消自己的席位。由于国王解散了议会,伯明翰同盟给他写感谢信。在他们看来,“国王……虽不在事实上,却在原则上是同盟的一员,他同意了同盟提出的每一项改革措施。”正因为如此,伯明翰同盟号召各地保持安定,说对改革最好的支持,就是什么都不要做,静等国王和政府放手改革!
大选结束后,政府得到134票的多数,下院的绝对优势建立起来了。6月24日,罗素提出第二次改革案,内容几乎与第一次完全一样。在辩论中,尽管托利党拼死抵抗,逐字逐句反复争夺,也尽管皮尔披挂上阵,亲自组织一次次反扑,但法案还是轻易通过,没有遇到多少麻烦。9月22日,法案提交上院。
反改革的托利党贵族,此时只有上院可以掘壕据守了,议会改革触犯利益最大的就是这些人,他们当然要拼死一战,准备借上院否决法案。
改革派的斗争一旦上院否决法案,辉格党政府应采取什么对策?兰斯多恩认为应当辞职,打退堂鼓,但下院改革派议员举行集会,谴责辞职即是背叛。当激进派议员提出应当册封足够数目同情改革的贵族,以迫使上院通过法案时,辉格党议员又不肯支持了。这种犹犹豫豫的态度使“中等阶级”大为不快,伯明翰的工业家们于是走到了运动的前列。
10月3日,伯明翰政治同盟召开群众大会。上午10时,伯明翰教堂钟声大作,各街道打铃召集居民开会。市民们纷纷放下手头工作,连妇女儿童也都关门闭户,到指定地点整队,前往纽豪尔山会场。同盟过去就与周围几十个地区有直接联系,此时为壮大声势,便召请附近约20个镇的代表与会。
那天上午,各地同盟纷纷打着自己的旗帜远道赶来,乘车的,骑马的,浩浩荡荡,甚是壮观。每当一地代表敲锣打鼓地进入会场时,在那里的群众便振臂高呼,响声如雷。近午时分,阿特伍德与同盟政治委员会成员前往会场,一路上人山人海,车水马龙。据大会组织者后来回忆说到会者有10万,一说 15万。这是改革高潮开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群众行动,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热情。
但这次大会并没有对上院起什么影响,10月8日,上院以41票多数否决政府法案,一场人民与贵族的对抗就由贵族老爷们亲手挑起了。当晚,伯明翰各教堂丧钟呜咽,通宵不息;首都改革派报纸套黑框刊载表决结果;消息传到各地,全国哗然,但此时政府却准备妥协了。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托利党贵族中分化出435一个温和派,以汪克里夫男爵和哈罗比伯爵为首,称作“动摇派”。他们唯恐长期对抗会削弱贵族的力量,造成政治危机,因而希望两党贵族捐弃前嫌,各作让步,团结一致,拯救宪政。政府也想与这个集团谈判,企图通过某种妥协,使上院通过温和的改革法。但“动摇派”
提出以下条件:1.提高选举的财产限制;2.保留较多的衰败选邑;3.不允许市镇居民参加郡县选区的选举,把城市和乡村截然分开,以保证地主对乡村的绝对控制。很明显,如果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中等阶级的利益将大受其害。
这样,中等阶级才重新想起:辉格党到底是贵族,斗争必须靠自己去赢得。
因此,在10、11月两个月中,中等阶级的活动骤然加剧。10月12日,在与政府会谈的当天,普赖斯就着手组织首都地区的改革派同盟,月底,成立了“全国政治同盟”。这个组织自称代表“各阶层”,实际上是旧中等阶级激进运动的中心。该同盟成立后,与伯明翰同盟密切合作。此后,“中等阶级”的两个分支就完全统一行动了。10月20日,伯明翰同盟号召各村各镇都成立组织,以加强人民运动的声势。这以后,各地不断有新组织出现。
如果说中等阶级的勃兴已使政府感到不安,那么工人阶级的活动简直就使整个统治阶级如坐针毡了。上院否决法案后,工人运动更加蓬勃发展。10月12日,曼彻斯特一万人集会,抗议上院行径。会上通过要求普选的决议,纯粹是工人的纲领。11月17日,里兹成立了一个工人改革派组织,提出普选政纲。在博尔顿,工人力量如此之大,以至在当地政治同盟第二次大会上,中等阶级竟退出会场。在伦敦,工人阶级全国同盟也加紧了活动。
工人中还发生了一系列自发行动,首先发难的是德比市。上院否决法案的当晚,该市群众袭击反改革派住宅,导致3人被捕。次日,大批群众包围市监狱,要求释放被捕者,守卫开枪打死1人。于是群众砸开监狱,放出囚犯,接着又去围攻郡监狱。群众与当局的对抗持续了3天,死伤多人,直到军队赶来才镇压下去。10月9日,诺丁汉市也开始闹事,群众举行盛大集会,接着便占领并烧毁了纽卡斯尔公爵的诺丁汉堡。11日,骚动继续蔓延,群众开始袭击工厂、花园等地,12日军队增援后才逐渐平息。类似的骚动在莱斯特、伍斯特、埃克塞特等工业城镇先后发生,但规模最大的是在布里斯托尔。
10月29日,市法院推事韦瑟罗尔从伦敦回城主持巡回法庭开庭式。韦瑟罗尔是个臭名昭著的反改革派议员,他回来的消息立刻引起严重骚乱。群众开始搜寻他,袭击他可能藏身的一切建筑。尽管他已爬房顶逃出布里斯托尔,当局也宣读了防暴令,群众的骚动仍无法阻止。军队不得已撤到郊外,暴动持续了3天。其间群众捣毁了市政厅、市议会、监狱、税所、海关、主教官邸、船坞等公共设施,损失估计达30万镑。3天后,军队重新控制局势,群众死伤数百。当军队冲进广场时,发现威廉三世的塑像上竟戴了个自由小帽。
这些骚乱充分显示了人民的力量。一个反改革贵族在达林顿附近被人认出来,只得跳下车落荒而逃,结果被堂皇的马车碾成碎片;伦敦德里侯爵被人围住,幸亏近卫军赶到才得以脱险;达勒姆主教被围在官邸里不敢露面;埃克塞特主教府则不得不由海岸警卫队把守防卫;皮尔自知道人怨恨,便在庄园里囤集军火,准备抗变;威灵顿也在住宅窗框上钉了铁条,以防围攻。
对辉格党来说,这些无异是提醒他们:后退是不行的,下层已经起来了,万一与中层联合行动,天下就不可收拾了!因此,布鲁厄姆警告说:“假如中等阶级反对政府,想做下层百姓的盟友,甚至只是在动乱时中立或无动于衷,镇压抢劫犯就完全不可能……须知,即使在伯明翰和其他一些地方,(政治)同盟也是由那些必然站在我们和亨特式、布里斯托尔式的打家劫舍者之间的人物组成的。”因此,稳住中等阶级就成了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而稳住中等阶级的唯一方法,就是不从原有立场后退。
布里斯托尔事件还产生一个奇妙的后果,中等阶级害怕了。他们担心万一动乱四起,军队会无力控制,布里斯托尔就是明证。于是他们开始谈论建立一支法国式的“国民自卫军”,以便在工人起义时用以自卫。11月初,伯明翰同盟指定一个小组委员会,研究同盟改组问题。委员会建议按准军事形式重组伯明翰同盟,总部下设支队或连,各配备军事指挥人员。阿特伍德并指示:暂时先不装备武器,但一旦需要,就要能拉出一支队伍。
中等阶级的武装企图引起了工人阶级的警惕,他们认为有产者拿起武器,无非是将枪口对准无产者,于是就越来越多地谈论工人武装的必要性。
10月底,“工盟”按军事组织改组,并宣布11月7日召开大会,号召全国工人团体在各地同时开会,争取普选权,推翻贵族制。它要求与会的工人各带1条2尺长的短棍以显示实力。消息公布后,有产者大惊。“全国政治同盟”立即宣布它也准备武装起来,托利党的报纸则号召贵族拿起武器,保卫教会和国家。这样,当时三种社会力量都号召武装起来,内战一触即发。
在这种情况下,格雷政府不得不采取果断行动。它相继采取了3项相关的措施。一是镇压工人。11月5日政府下令取缔“工盟”预备召开的大会,否则将强行镇压。二是拢络中等阶级,劝说伯明翰同盟放弃武装计划。结果, 11月21日同盟宣布不准备武装,政府则宣布一切群众武装为非法。最后,政府为重新取得中等阶级的信任,中止了与托利党“动摇派”的谈判。12月 10日,双方最后一次会晤,政府故作冷淡,结果不欢而散。政府的妥协企图到此为止,辉格党终于未敢倒退。两天后,政府拿出第三个方案。和前两个相比,虽然有所不同,但在原则问题上丝毫没有退让。13日,伯明翰同盟声明对提案完全满意。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英国两次避开了革命危机。
这个法案很快在下院获得通过,并于1832年3月26日提交上院。如果上院再次否决法案,政府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马上册封50名新贵族,让改革派在上院取得优势;要么辞职,让托利党组阁。辉格党希望第一种前途,但国王未必肯这么干;万一国王不肯,就只有第二种前途了。由于“动摇派”
投票支持,法案于4月4日通过二读。但威灵顿早就声明他将率领顽固派顽抗到底,因此当法案进入小组委员会阶段时,摊牌就在所难免了。5月7日,托利党贵族林德赫斯特的一项动议获得胜利,迫使政府立即摊牌。当日晚,内阁要求国王册封足够的贵族以确保法案成功,否则就辞职。次日晨,国王通知政府“接受他们的辞呈”。改革斗争中最激动人心的一幕开始了。
伯明翰同盟本以为改革已绝无问题,直到4月底,他们才觉得事情不太妙,因此决定5月7日召集群众大会,同时决定:一旦法案失败,他们就要 “永不终止地运用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合法手段,争取更全面更有效地恢复人民权利,而不仅仅满足于改革法打算给予的那一些。”大约有10万至15万人参加了大会,同盟二号人物帕克斯在会上说:他相信“假如格雷勋爵被赶下台,或者法案被扼杀,全国各地的政治同盟将3倍、4倍地增长。”他还说,他“但愿”事情不要发展到“用内战和武力抗争的最后手段来争取自由,或是用不必要的革命恐怖来影响英国贵族”的地步,因此,他“恳请上院不要把内战强加给改革派。”但大会开晚了,大会刚刚结束,政府已经失败了。5月10日晨,政府辞职的消息传到伯明翰,紧张的气氛顿时笼罩全城。同盟会员自发向总部集中,默默地守在门口,等待领袖们作出决定。5月10日上午,阿特伍德赶到同盟,他命令会员们摘下身上佩戴的会徽,因为会徽上有英国王冠。下午,同盟在新厦山召开第三次大会,附近人民陆续赶到,聚成近10万人的人群。前两次大会的节日气氛不见了,到会的多是男子,仿佛在应征出战。阿特伍德号召耐心等待,随后写出请愿书,派人立即送往伦敦。
各地改革派反应强烈。5月9日,“全国政治同盟”召开群众大会,要求议会在辉格党政府复职前停止财政拨款,这一要求立即获得全国支持,各地请愿书都写上了这一条。在5月9日至19日的10天危机中,全国召开了 200多次群众大会,呈交300多份请愿书。成千上万的人涌进各政治同盟,仅9至12日参加“全国政治同盟”的就有5000人。
5月12日,国王宣布由威灵顿组阁,危机迅速激化。当日,各地改革派代表赶到伦敦会商对策,随后伯明翰代表与普雷斯会谈。许多年后,普雷斯声称他当时与帕克斯商定了武装起义计划,约定一旦威灵顿组阁成功,伦敦就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制造动乱,拖住7000正规军;伯明翰则乘机发动革命,与全国联系,成立临时政府。
工人阶级的态度是革命发生与否的重要因素,五月危机是工人态度最积极的时期。也许他们意识到托利党组阁会对他们更不利,因而对改革法的热情突然高涨。5月10日到18日,工人阶级全国同盟不断召集群众大会,反对托利党组阁。在会上发言的人措辞激烈,他们提出了许多行动建议,其中包括抗租、抗税、银行挤兑,以及一旦托利党建立政府,就抵制他们可能提出的一切改革方案等等。会上有人甚至提出“不是改革,就是革命”的口号。
5月14日,曼彻斯特的产业工人与工厂主联合召开10万人大会,会场就在当年彼得卢大惨案的旧址。由于意识到改革可能前功尽弃,当年无情屠杀工人改革派的曼彻斯特工商业主被迫在口头上承认了彼得卢大会的基本原则 ——普选权,这是对历史的极大讽刺。据记载,双方的协议为:“一方承认人人有权为议会所代表,另一方则把目前的要求限于改革法,保证不提出基于更激进原则上的改革建议。”值得注意的是,连一贯反对工人阶级支持改革法的《贫民卫报》,也表示出一种积极的态度:只要中等阶级把工人当作 “朋友和兄弟对待”,“真心诚意地主张完整的法案,并坚持争取自由人的公正、平等和真正的权力”,“我们就将帮助他们取得自己的权利”。而在此之前,直到5月12日,即宣布威灵顿组阁的那一天,《贫民卫报》还在号召工人阶级“袖手旁观”,“不参加战斗”。可见一个托利党军政府的现实危险,正在把利益不同的各阶层都联合在一起。在整个改革法斗争中,只有五月危机时表现出工人阶级愿意与中等阶级结盟,并采纳共同的纲领。同时,也正是在五月危机中,工业资产阶级开始承认工人阶级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因此可以说,五月危机发展下去,很可能出现法国那种中下层人民联合作战的情形,因此这个时候是英国最接近于发生革命的一个时期。
面对“暴动”或“起义”,中等阶级实际所做的仅仅是经济制裁。威灵顿受命组阁的当晚,普赖斯提出“取黄金,阻公爵”的口号。一夜之间,这个口号就贴满伦敦内外,并迅速传向外地,引起大规模黄金挤兑。据估计,英格兰银行原有黄金储备300—400万镑,10天内提出160万镑,几近一半。
有人说5月18日格雷觐见国王前,英格兰银行代表请他转告:若危机延续下去,4天内黄金储备就会枯竭。因此后来有人说威灵顿是被黄金挤兑挤掉的,这话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五月危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表面上局势高度稳定,这与前一年的十月危机形成鲜明对照。这种平静使统治阶级格外害怕。统治阶级第一次感到局势捉摸不定,深怕不知不觉中爆发革命。这一切又因改革派议员加强了议会攻势而显得更加可怕。5月14日,下院通过决议,宣称下院将永远不接受由托利党政府提出的任何改革建议。这使人想起长期议会。下院表明如果托利党组阁,议会将和他们发生持久冲突。同一天,伯明翰同盟发表“庄严宣言”,要求国王召回格雷,号召全国人民在宣言上签字。宣言送往全国,指望得到 400万人的签名。
但这已经不需要了。托利党首领在议院内备受围攻,在议院外压力重重,皮尔不肯入阁,威灵顿终于承认组阁失败。5月15日,威灵顿交回委任状,建议国王召回格雷。国王则在辉格党的强大压力下立下书面保证,表示一旦需要,他就会应内阁的要求,在任何时候册封任何数目的贵族。此后,有影响的托利党人都退出上院。他们知道大势已去,便激流勇退。事实上不退也没有其他出路。
1832年6月4日,法案在上院通过,3天后得到国王批准。经过18个月的艰难奋战,改革终于成功了。
改革的结果根据改革法,55个衰败选邑失去选邑资格,另外30个选邑各失去一个议席,这些被剥夺的席位有的分给较大的工业市镇,使工业资产阶级能够向议会派出代表;有的则分给郡县,使人口较多的郡可以多选出一些议员。在选举权方面,除原有的40先令自由持有农外,农村选区收入在10镑以上的公簿持有农、长期租约农,以及收入在50镑以上的短期租约农及交租50镑以上的佃农也获得了选举权。在城镇选区,选举资格划一为年值10镑以上的房产持有人,原有的选举权可酌情保留。选举权方面的改革使城乡中等阶级大部分成为选民,从而获得了政治权利。在工业城镇,工业资产阶级控制了本地选举。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则完全被排斥在选举权之外。由于1832年的改革,全国选民人数从1831年的48.8万人上升到1833年的80.8万人,由占人口比例的约2%增加到3.3%。
1832年改革是人民斗争的成果,英国人为争取改革成功,已前赴后继地战斗了好几代,其中有牺牲,有流血,有痛苦,有眼泪,但最后是人民的意志胜利了,人民的意志不可抗拒。1832年改革又是各阶层共同奋斗的结果,从辉格党贵族到中等阶级到苦难的工人阶级,尽管他们要求改革的目的各不相同,但在改革这一点上结为联盟,使改革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这次改革是英国中下层人民为打破贵族地主阶级垄断政治权力的一次联合行动。在改革中,各阶级都为自己的利益和权利而战,因此改革过程本身就充满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然而改革只使中等阶级取得参与政治的权利,使他们置身于 “统治阶级”的行列。这以后,政治斗争的焦点不再是“人民”与土地贵族的矛盾了,而是没有权利的劳动人民和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地主、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英国的阶级阵线改变了。
通过改革,资产阶级(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中等阶级”)取得了选举权,但他们并没有掌握国家政权,政权仍在贵族手中,资产阶级仍处于从属地位。
但贵族不再能垄断政权了,资产阶级不满足于自己的配角角色,他们从已取得的成果出发,发动新的斗争,争取更大的权利。这是理解1832年改革后,资产阶级发动新攻势(例如反谷物法运动)的关键所在。
工人阶级在争取改革的斗争中出力最大,结果却一无所获。他们被整个剥削阶级排斥在权力之外,成了唯一无权的阶级。这使工人阶级为自己的权利继续斗争,于是就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宪章运动之所以是纯粹的工人阶级运动,其原因大概也就在此。
1832年改革是一次和平的改革运动,它证明在工业资本主义443的条件下,改革之路在英国仍能行得通。这就为英国以后的历次改革开创了先例,以后的改革也就不再这么艰难。1832年改革打开了通向民主之路的大门,但民主的道路并没有走完,它还要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才能最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