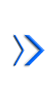一、大卫·李嘉图和边沁
大卫·李嘉图和边沁是19世纪初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理论家。他们的理论为工业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摇旗呐喊,因此随着工业资产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逐渐上升,他们的学说也越来越具有官方的性质,成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学说。
李嘉图(1772—1823)是伦敦交易所一个犹太经纪人的儿子,家中十分有钱,14岁时他就随父亲去交易所做事,深得其中的奥妙。后来由于与信基督教的女子恋爱,遂与家庭决裂,一个人单独去做交易所生意,在这些活动中大发其财,成为腰缠万贯的巨富。以后,他研究自然科学,与别人共同创建地质学会,但很快就转向经济学研究,发表有关经济问题的论文。1819年,他当选为议员,在议会中屡次发言攻击谷物法,主张自由贸易,是工业资产阶级在议会的代言人。
李嘉图的成名之作是《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发表于1817年。这本书全面阐述了他的经济思想,是一本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大成的学术著作。李嘉图继承亚当·斯密关于价值的学说,认为劳动时间是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但他指出在这方面亚当·斯密并不彻底,因而造成经济学理论的混乱。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他在对亚当·斯密的批判中发展了他的理论,指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认为在相同单位时间里,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所产生的价值不同。他还把劳动分为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指出只有直接劳动才能产生价值,间接劳动只是把原有的价值转移到新生产出来的商品中去。他还认为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每个生产者实际上所耗费的劳动,而是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要的必要劳动。从这一点出发,他指出资本本身并不产生价值,作为资本的形式的生产资料,在生产中只能通过工人的劳动把原有产品中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而新的价值只能由活的劳动才能产生。他的这个观点后来被工人阶级所接受,成为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理论根据。
但李嘉图并不考虑利润的存在是否合理,在他看来,利润是天经地义的事,资本家既在生产中投放资本,理所当然应取得利润。他认为资本主义是地久天长、从来就有的合理制度,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没有任何可值得怀疑之处。他认为资本在原始社会就已有之,正因为如此,他不区分生产者自己所有的生产资料和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而把它们一概称为资本。
李嘉图的研究重点在产品分配方面,正是通过这些研究,他天才地看出了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三大阶级的对抗。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序言中一开始就说:“劳动、机械和资本在土地上面联合使用,所生产的一切土地生产物分归社会上的三个阶级: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地主有土地、资本家有耕作土地的资本、劳动者则以劳力耕作土地。”全部生产物就在这三大阶级中进行分配,一部分以地租的形式分给地主,一部分以利润的形式分给资本家,劳动者则取得工资。他认为“这种分配,支配于一定法则,确定这种法则是经济学上的主要问题。”他认为工资是由工人及其家庭所消耗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决定的,利润是支付工资后商品价值中所剩余的部分,地租则是农产品中超过工资和利润的那部分价值。他认为在现实的分配过程中,这三种分配形式在量上此消彼长,这就使社会上三大阶级的经济利益互相对立。他指出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工资增长则利润减少,利润上升则工资降低,因此工人和资本家利益不同。他认为地租是上、中等土地的出产物多于劣等土地出产物的结果,地主从这个差额中获取地租。然而由于人口增多,粮食需求量不断增长,最劣的土地也必须耕种,这就使地租必然增加,并造成农产品价格提高,而这就会导致工人的货币工资也随着增加,于是资本家的利润就会减少,因此,资本家和地主间也存在利害冲突。但是在地租和货币工资都有增长时,地租取得真实的增长,工资却只有虚假的上升。
因为工资增长跟不上谷价的上涨,结果货币工资增加了,实际工资却在下降,工人对谷物的支配权反而减少。所以,工人与地主的利益也相互对立。这样,李嘉图就看出了当时三大阶级彼此对抗的三角关系,对当时的阶级状况作出了真实的描述。但李嘉图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地主阶级,因为在他看来,地主取得地租纯粹是不劳而获。只要谷价上涨,即使最劣质的土地投入使用,都能使自己的收入不断增加,因此,这是一种不义之财,而且地主阶级还利用政权人为地提高谷价,增加自己的收入。与此同时,地租增加会使利润减少,实际工资收入也会减少,这样就妨碍了工业的发展,而工业才是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由此可见,李嘉图是站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说话的,在他的社会冲突模式中,资本家和工人有共同的敌人,这就是地主阶级。李嘉图的这种看法,反映了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事实。
如果说李嘉图是经济学中为工业资产阶级呐喊的代言人,那么在政治学中就要数边沁了。杰里米·边沁(1748—1832)是伦敦一个讼师的儿子,12岁就去牛津学法律,但不久就发现自己对当时流行的习惯法规则十分反感,于是决定致力于法学研究,企图创立一个“科学”的法律体系。他一生写了许多法学和政治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有《道德与立法的原理》、《惩罚与奖励的理论》等。在这些著作中,他提出功利主义的政治学说,认为这是建立一个理想社会的基本出发点。
边沁反对自然权利的政治学说,认为自然权利的概念混乱不堪,没有明确的定义,任何人都可以作出自己的解释。他对“社会契约”也提出质疑,认为国家的建立是靠暴力,而其延续是靠习惯,根本不存在“社会契约”这种东西。既然如此,理想社会何以实现呢?他认为必须依靠功利。边沁从“苦”
与“乐”着手阐述功利。他说人的本性是避苦求乐,追求幸福是一切人生而有之的自然本能,因此,避苦求乐是一切人类行为的基本出发点,是自然的法则。而这种避苦求乐的天性就是“功利”,于是功利便成为衡量人类行为的基本标准。但每个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幸福时,有可能与别人的“乐”发生冲突,人类的欲望并不总是和谐的。而且,由于道德等原因,人的行为还会有对错之分,错误的行为并不符合功利主义原则。既然如此,用什么来判断人类行为的正误呢?由此,边沁提出他的学说中最有名的一个论断——“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认为这既是判断个人行为的准则,也是评判国家行为的标准。在判断个人行为时,只要其行为不与这根本的准则相冲突,就应该被看作是合理的;而国家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时也必须以此为标准,为社会上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限度的福利。
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实际上是在为工业资本主义寻求理论基础。根据边沁的说法,一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幸福时,只要他的活动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有利,即使其出发点完全出于私利,他的活动也获得了合理的基础,而工业资产阶级在追求自己的利润时,情况正是如此。国家若推行有助于工业发展的政策,也能够取得相同的效果。由此可以看出,边沁学说反对的是贵族地主的特权和商业资产阶级的垄断,他在为自由竞争争一席之地。
边沁认为个人的功利与社会的功利也可能发生矛盾,为解决这个矛盾,功利主义从两个方面着手。首先,边沁认为在一切利447益中只有个人利益是真实的利益,社会利益只是个人利益的总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集体的幸福寓于个人幸福之中,无数个人在追求自身的幸福时,就会形成一种总体幸福。所以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之间虽有差别,但这种差别却是可以沟通的,而沟通的手段就是国家。由此边沁的功利主义进入第二个论题:关于国家。
边沁认为国家要沟通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就必须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出发制定政策。根据这个原则,他主张积极的政治参与,主张人人都有选举权,让每一个人的要求都能明确而及时地反映出来,以便国家在制定政策时考虑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愿望。他因此支持议会改革,宣扬民主政治,反对不合理的议会选举制度。边沁的这种态度曾给中等阶级激进派以巨大鼓舞,并为中等阶级的激进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后来大多数中等阶级激进派都是从功利主义立场出发大力宣传议会改革的。在这方面,边沁有重大的影响。在边沁的政治思想中,国家除了能沟通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外,还具有能干涉个人利益的一面。他认为国家和法律就本质来说都是一种恶事,是万不得已才建立和制定的。但国家和法律又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国家,就不能维护社会和平,没有法律,就不能保障个人安全。法律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法律代表的是惩罚,即“痛苦”;人在避苦求乐的追求中惮于受法律惩戒之苦,就不得不遵守社会准则,在社会许可的范围内行动。但国家既有这种强制的性质,也就有可能用强制的手段来干涉每一个人的幸福,所以国家的权力必须加以限制,使其保持在最低限度上,不妨碍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为此,边沁认为国家的立法只应针对“公益的道德义务”,也就是社会的事;而对“自己的道德义务”,即私人生活方面,国家不应横加干涉,而应让每个人自己去处理。由此推论,国家就不应该对工作时间、工资数额、劳动条件等等个人的事务制定立法。正因为如此,功利主义者在经济政策方面主张“自由放任”,支持济贫法,反对工厂法。因此,功利主义深受工人阶级的怀疑。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功利主义的阶级性质十分明确。它坚决反对地主阶级的政治特权和社会特权,并不顾及工人阶级的特殊利益,是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在政治学说上的反映。但功利主义又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它不仅为反对贵族垄断政权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而且体现了正在上升的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和愿望。它又是理性主义的突出成果,它把人的现实需要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这显然比那些把希望寄托在“千年王国”的到来上的神学教谕高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