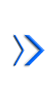毕加索作品赏析——超现实主义时期系列
很快,毕加索步入了他生命中最神秘的“超现实主”探索,当撕裂的造型(《格尔尼卡》)、深邃和凶残(《女主角》)代替了以往的忧郁或是怪诞的时候,毕加索的生活也陷入了一个个的旋涡。他开始以放荡不羁的个人形象展现在公众面前。女人们在这个狂暴、贪婪的男人身上渴望着分享他的艺术灵感与名气,但她们得到的却只是虚无而残酷的现实;相对感情而言,毕加索更看重她们的身体,为了使她们在使他娱兴之余成为他听话的创作工具(《哭泣的女人》、《自我陶醉的女人》),他甚至使用了许多令人瞠目的低级手段。
超现实主义以精细的细部描绘为特征,通过可以识别的经过变形的形象和场面,来营造一种幻觉的和梦境的画面。笔触的变形、扭曲和夸张以及几何彩块堆积、造型抽象,表现了痛苦、受难和兽性,如《格尔尼卡》。
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是毕加索创作的超现实主义时期,其创作特点是将生与死,梦境与现实统一起来,具有神秘、恐怖、怪诞的气氛。这时期的作品包括《雕塑家》等。
1924年,毕加索重拾对立体主义的兴趣,一种新的、狂乱、冷酷的风格在这个时候悄悄展现。第二年夏天,在布列塔尼半岛绘的画作中,出现了一类新型立体主义风格的静物作品赏析——清澈的光线浸入整个画面,呈显某种纹路般的律动感,好似水流底下的景象。这种被渗滤出来像线条式的透明感,犹如那从百叶窗帘的缝隙之中,透出的一道道光芒……
随着社会地位和知名度的提高,奥尔迦变得越来越极端,以前她所关心的是上流社会对她的关心和崇敬,而现在她要在走下坡路的婚姻中抓住丈夫。而当她所得到的关心越来越少时,她怒不可遏,朝丈夫发泄。对于奥尔迦的做法,毕加索由生气而愤怒,由愤怒而狂暴。两人的裂痕越来越大。由此而诞生了《三个舞者》。《三个舞者》在像是被欲火或疯狂折磨不已的畸形身躯上,显示出一种新奇费解的暴力。画面色彩的感觉十分激烈,三名舞者像是受酷刑一般,脸部的线条扭曲。从不同层面来看,这幅画写状残忍如挥不掉的梦魔一一恐怖的面容、像动物鬃毛般的头发、铁钉状的手脚指头……完全不同于画家先前那幅乖巧小儿肖像《穿着百袖服的保罗》。
每当毕加索欲表达某种情感,无论激烈或温柔,均在画里实现。不料《三个舞者》当真掀起狂涛,但各方反映是毁誉参半。对熟悉他画风演变的人而言,这幅作品意味着毕加索断然决裂以往精熟的手法,发展出难以预料且挑衅味强劲的新绘画路线。
奥尔迦并非这股暴力的惟一原因,决裂背后还有另一个诱因,来自超现实主义运动,这项文学、文化运动从1924年起,如汹涌潮水猛烈地扩散。
超现实主义宣称:“美是痊孪病态的”战争后遗症为全面性的,艺术上亦不例外。立体主义绘画的暴力感虽引起厌战情绪的强劲反弹,但也促成否定传统艺术的达达运动兴起。美术运动百花齐放,毕加索感觉超现实主义与自己最相投。
超现实运动发起人有艾吕雅、蒲鲁东和阿拉贡。他们希望该团体是所有现代思潮的诠释者,打着“要求新的人权宣言”口号,自办《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在杂志创刊号里,刊出毕加索1914年“结构”系列的一件作品。这个由诗人与画家组成的超现实主义团体,不断成长,重要性愈来愈强。超现实主义运动成员无不期望,当寻觅梦中和潜意识下各类异象的同时,还能深触艺术创作的根源。波德莱尔、马拉梅或罗特雷亚蒙等诗人着手尝试的理念,却由毕加索放手实践。
蒲鲁东写道:“美是痊孪病态的。”当时,哪有一幅同期画作比《三个舞者》更能诠释这句名言?蒲鲁东因而诠释“超现实主义”:“从毕加索那儿,我们同意某种身体的自动性,与做梦状态几乎一致。”而毕加索如何能不被这个新兴的主义吸引?他从不放弃绘画及观察事物形上、形内二面。他永远不会画事物在“现实中的相貌”,而是画它们“现实上的状态”,和蒲鲁东称的“心理模型”如出一辙。
1926年春天 ,毕加索开始制作《吉他》系列,全用布料、绳线、生锈铁钉及织毛线棒针等素材,拼凑成侵略感十足的作品。与和谐、品位、规矩等概念绝裂,物品的实际用途亦遭改变。毕加索以其独特方式,来扮演超现实主义者。
虽被超现实主义团体吸引,但毕加索的超现实风格创作并不受这项运动局限。此外,常往来的也非这个团体中的画家,而是日后结为好友的诗人。1925和1926两年间,超现实主义运动兴起,促使体内早已潜伏的暴力和推翻现状倾向越来越激烈,一切都将改变。
到了20年代中期在美术界又兴起了“未来主义”。未来主义认为现代的艺术,应该表现出机械革命的速度、运动、暴力和音响。同时期的流派还有“先锋派”。行行色色的文艺理论和实践使这个时代变得不同反向。置身于其中,毕加索也受到了影响。性、爱情、同性恋、兽与人、梦幻、精神分裂等题材都出现在过毕加索的画中。
奥尔迦的病情不断加重,她会经常性向毕加索发泄某种内心的怨愤,有时突然冲进毕加索的画室,捣乱他的环境,破坏他的画作,甚至搅乱他的创作思路。奥尔迦无休止的干扰,使得毕加索的思想和情绪也变成了轻度的荒谬和错乱。在他的画作中也经常会出现丑恶的女人形象,畸形的身体,痛苦的表情。或是呼喊着的孤独形象。毕加索陷入了烦恼中,他觉得自己无处可逃,在这个无形的大网中挣扎。他们的婚姻也注定要走向失败。
1927年初,毕加索路过巴黎豪斯曼大街的一家商店,被橱窗前站着的一位少女迷住了。她棕色的皮肤,挺直的希腊式的鼻子,灰蓝色的眼睛,高高挺起的胸脯,有一种北欧女子特有的魅力。这位姑娘就是玛丽·德瑞丝。当时玛丽·德瑞丝只有17岁,她身上勃发着的青春和活力使毕加索无法抗拒。在玛丽刚过完18岁生日的时候,毕加索就背着奥尔迦开始了与她的秘密交往。毕加索开始了他一生中最无节制、最无顾忌的生活,而玛丽对毕加索绝对服从,是他独占的一件物品,是他力量和性吸引力的证明。这期间,毕加索用华丽的色彩,梦幻般的调子创作了许多幅玛丽·德瑞丝的肖像画。其中一幅为《坐在安乐椅中的女人》。
1931年,毕加索在巴黎不远的乡野,买下一座17世纪建造的花园古堡。古堡位在景色怡人的布瓦热卢小村边缘地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造型优美的哥特式小教堂,接着是一片偌大的庭院,再则是浅灰墙面、深灰屋顶的巨型宅第。最吸引毕加索目光的却是庭院边的马厩,他将工作室设在那儿。他和玛丽搬到那儿,终于避开了奥尔迦的无休止骚扰。几个月后,玛丽为毕加索生了一个女儿,毕加索为她起了自己去世的小妹妹的名字:玛雅·劳拉·孔塞朴松,但她的出生登记上,父亲一项却填着“不详”。之后毕加索为她画了《玩球的浴女》,把她的美丽凝固为永恒。《梦》这幅画作于1932年,可以说是毕加索对玛丽精神与肉体的爱的最完美的体现。
玛丽同毕加索的关系公开后,毕加索卷入了一场与奥尔迦离婚的官司之中。他在一个朋友面前曾说过:“牛的眼睛,有上千条理由保持缄默,对那喝多了咖啡而撒尿如雨的跳蚤,尽可视若无睹。”在这里,“牛”是他自己的代号,“跳蚤”显然指的是奥尔迦。正当毕加索心乱如麻,感到很茫然的时候,退出了他的生活圈长达21年之久的费尔南德在杂志上刊登了她与毕加索之间回忆录的第一篇摘要。毕加索非常恼火,愤怒之下,他创作了四幅极有力而动人的铜版画《瞎眼的米诺陶》,在画布上,迸发出了自己全部的情绪。牛首人身的怪物又一次成了他自己的象征。他想尽快摆脱奥尔迦,但由于毕加索是西班牙人,无法回到弗朗哥独裁统治下的西班牙去办理离婚手续,他们之间的婚姻只好以分居形式宣告结束。
几乎就在女儿出生的同时,五十三岁的毕加索又遇到了另一个情人多拉·玛尔。年轻迷人的多拉·玛尔与毕加索名作《阿维尼翁的少女》同年出生,多才多艺,既是画家、摄影家、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文化缪斯,又是模特。1935年她与毕加索在一家咖啡馆相识,此后开始了长达8年的恋情。在他们火山般热烈的情感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心灵间的巨大默契。多拉可以很有见地地谈论科罗的摄影试验,谈论这些试验如何运用到毕加索的绘画中,谈论毕加索脑子里思考的技术问题和哲学问题,她能分享他的种种思想,他的朋友也是她的朋友,她是毕加索唯一一位能称得上红颜知己的女人。在西班牙内战和德军占领时期,他们一起住在巴黎大奥古斯坦街的一座画室里。而多拉·玛尔也用她的相机记录下了毕加索这一时期的创作和生活,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她最为之骄傲的是他们俩合伙创作的一幅画,联名署着“毕加玛尔”。
1937年,西班牙的格尔尼卡小镇为德国法西斯空军夷为平地,毕加索闻讯后极为愤慨,就为巴黎世界博览会西班牙馆画了《格尔尼卡》这幅壁画,对法西斯暴行表示强烈抗议。此画结合立方主义、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风格表现痛苦、受难和兽性:画中右边有一个妇女举手从着火的屋上掉下来,另一个妇女冲向画中心;左边一个母亲与一个死孩子;地上有一个战士的尸体,他一手握剑,剑旁是一朵正在生长着的鲜花;画中央是一匹老马,为一根由上而下的长矛刺杀,左边有一头举首顾盼的站着的牛,牛头与马头之间是一只举头张喙的鸟;上边右面有一从窗口斜伸进的手臂,手中掌着一盏灯,发出强光,照耀着这个血腥的场面。全画用黑、白与灰色画成。这幅画描绘了西班牙小镇格尔尼卡遭德军飞机轰炸后的惨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将领和士兵经常出入于巴黎的毕加索艺术馆,争相观看毕加索的艺术。可是这些不不速之客受到了冷淡的接待。有一次,在艺术馆的出口处,毕加索发给每个德国军人一幅他的油画《格尔尼卡》的复制品。一位德国盖世太保头目指着这幅画问毕家索:“这是您的杰作吗?”毕加索面色严峻地说:“不,这是你们的杰作!”
战争结束后,他以法国抵抗运动战士的荣誉参加了战后第一次美展,并于1944年加入法国共产党。以后,他又参加保卫和平运动,为世界和平大会创作了宣传画《和平鸽》。毕加索为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毕生的努力。
在毕加索与多拉相处的最后几年中,个性都很强烈两人渐生龃龉。毕加索经常殴打多拉,许多次打得她躺在地板上不省人事。1940年6月,毕加索创作了一幅最凶暴的最有复仇意味的妇女形象:以多拉为原型的《裸体梳妆女》。从奉为掌上明珠到任意践踏,从纵情作乐到恣意毒打,在给多拉所作的一幅幅狗面的画里,他完全把女人变成了驯服的动物。毕加索对朋友说: “我不爱多拉”,对多拉说: “我爱你是因为你像个男人!”“你并不美……就是会哭!”于是多拉放声大哭,毕加索就再继续画《哭泣的女人》。毕加索和多拉这种时晴时雨的关系,持续了六、七年。一九四二年毕加索画的多拉已精疲力竭,不再哭泣,而是痴呆茫然地看着什么。1943年毕加索离开了多拉·玛尔,分手时赠给她一套法国南方的住宅作为纪念。从此以后,多拉一个人孤单地在巴黎圣母院的倒影下,在塞纳河凄迷的林阴小道上消耗着自己的华年,直到五十年后的1997年7月,她以自杀为手段,给自己的生命画下“完美”的黑色句号。
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惨岁月之后,毕加索曾反复表示他已经与古典世界重新进行对话,他时而注意庞贝绘画(他是1917年访问意大利时了解到的),时而注意粗糙笨重而又意味深长的远古时期的雕塑,时而又注意米开朗基罗之后和拉斐尔之后的矫饰主义文明的纤巧细腻。他曾歪曲人的形象并讥笑有关比例的古典准则,他也曾拒绝对美要有先入为主的理想。但这都无关紧要,因为他毕竟一直在重新采用具有明显的再现物象价值的画法,况且这些画法又是运用到从古典角度考虑形体的和谐平衡的构图结构之中的。
毕加索在从事这种“雕塑式”的描绘物象的绘画同时,用更长时间进行立体主义的创作。在这方面,色彩重又在明亮部分的光彩夺目中闪烁出光辉,而明亮部分在色彩总体中又掺有庄严肃穆的色调。此外,在这些年间,人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花更多的时间在谈论“重新建立新秩序”的问题;同时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表示需要重新整理战前疯狂创新的经验成果,需要为立体主义危机找出新的出路。
1925年,这位西班牙画家终于在以具有激烈的论战性和浓厚的革新色彩的巨幅绘画《三个舞蹈者》对这种退化局面作出了答复。当然,这是立体派写实的复苏,是按照艺术家对现实的设想来对现实进行思想上的塑造。但是,这幅作品却不像战前的作品那样具有明确的理性,它所表现的是感情的暴烈冲动以及内心的绝望挣扎。这三个虚幻的人影是支离破碎的,从种种视点多次显现,并且在同一时间内在不同距离显示其形象,这人影正是内心世界的戏剧性反映,而画家则把它表现在画布上。
他在同一时期对超现实主义所作的探讨,也在思想的启发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特别是由于他与艾吕雅和布雷东交往甚密的关系;但这不过是一种相互关系,因为正是那些超现实主义画家,尤其是马克思·恩斯特和米罗,从毕加索的作品中获益匪浅。毕加索给那些超现实主义者上了一课绘画语言,作了重要的教导,教导他们如何依照脑海中对现实的想法来自由地运用造型方式:因为他意识到,已被掌握的现实只能是容纳内心世界的现实,而所有那些外在的、属于外界的东西则只能通过再现物象的办法来加以认识。
从这时起,他的作品就都变为“内心独白”的篇章了,这是他面对日常生活中最平常的事件,同样也是他面对人之所以活着的根本原因所产生的感情状态的既清醒又热情的分析(人的一生包括生与死、爱与性、暴力与同情)。在这激动的独白中,没有一点强调理智或象征情调。外在世界丧失了意义,以便让更隐秘的其他方面能显现出来,让人看到肉眼所看不到、但内心中却能感到和看到的东西,它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但就艺术家来说,把它加以忠实地再现就似乎是徒劳之举了。艺术家宁可创造一个形体,尽管它与客体并不想像,却与艺术家本身的感情和他对该物体的想法和想像一致。
1932至1945年可称为毕加索创作的蜕变时期。这一时期的艺术特点是,画作多为立体主义、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手法相结合的抽象画。以剧烈变形、扭曲和夸张的笔触以及几何彩块堆积抽象来表现痛苦、受难等感觉。作品包括《坐红色扶手椅的女子》、《朵拉·玛尔肖像》等。(1924-1937)